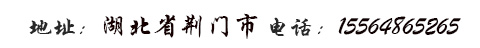小说杨红初恋笔记一
|
1 小梅当时低我半头。个不算高。头发带点自来卷。阳光打下来,她每根头发都像镀了浅浅的红铜,发点红亮的色。她额头浅短,头发虽往后拢,太浓密的缘故吧,高高的垫在额头上,像戴个洋式贝雷帽。她辫的两条齐肩小辫,松软得像发糕,和她浅红的皮肤,弯弯的眉,眼角下斜的长睫毛眼,翘短的鼻,细薄的唇一搭,有一种异域的丽质了。 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也都看出了这个特点,噢噢的乱唤小梅:红毛女—— 小梅家的电业局家属院,在我们捉马村东南头的斜对过,和我们遥遥隔着那条汽路。我们太行中学又在我们捉马村的东北角。上学,我和小梅在我们捉马村口那段汽路会合,一起顺汽路北行半里地光景,丁字路口东拐,再顺汽路走小半里地,就到了。放学,我和小梅在我们捉马村口那段汽路分开。各回各家。 不管上学放学,一见面,我们俩都像隔了好多年未见,攒下的话似那些年用电光挂历纸卷的珠光门帘,一串串的。小梅说话也像电光挂历纸串的珠光门帘,有种水润润细滑滑的质感。我猜着她这带点上海味道的口音是胎带的也未可能。 也早听说小梅是抱的。抱的上海育婴堂的。小梅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世,我也没敢问她。她总说她和她爸妈隔了两张皮。她爸妈都是电业局的工程师,都是那种咬着舌头尖说话的上海人。都戴眼镜。她爸瘦高,戴一副断腿的黑镜框眼镜。眼镜断腿的地方缠着鼓鼓的绝缘黑胶布。乍一看,他爸刀条脸的一边像肿了个瘤。镜片一圈一圈往里旋,他爸看东西还是嗡在鼻尖上。像暴露了身份的特务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她爸总是那副有点诡异的可笑样。她妈稍有些胖,常年在脑后盘着个发髻,脸也白净净的,眉眼细小小的,戴的红地蛋黄花纹的镜框眼镜也还可以,就是镜片上半段往里旋,下半段往外旋。她妈喜欢穿双排扣衣裳。军大衣,泥大氅,涤纶格子外衣什么的都是双排扣。那扣是接近本色的有机玻璃,坠在她妈的衣裳上,格外亮眼。帆布工作衣,她妈也改成双排扣,连袖口都坠着双排小黑扣。我们这个城最早一双枣红半高跟皮鞋,是小梅她妈蹬的。 因为这,小梅她妈有了个很响的雅号:“半高跟”。 “半高跟”推着辆凤凰红电光斜梁女坤自行车。当年,我们这个城的物资局只进了这样一辆自行车。手里有“号”的多的去了,结果,“半高跟”特批了这辆自行车。为此,“半高跟”成了我们这个城的名人。 “半高跟”来我们太行中学。她那双枣红半高跟皮鞋吧嗒吧嗒踩着我们教学主楼前灰砖砌的蜿蜒的路,很引起了一些骚动。教室的玻璃窗上嗡的都是扁脸。 她的手蓬在额头,往我们教室里眊。那张白嫩嫩的满月脸上勾的一双灵媚的眼映在我们教室的一扇窗上,她又做那种显痕露迹的有分寸的笑…… 算轰动了。 大虎,二狗,三猫都是我们初十一班的。他们的海军部队家属院,在我们捉马村南边,和电业局家属院东隔汽路,也斜对过。我们走路。他们一干男生有时候走路,有时候偷骑家里的自行车。他们走路,都不好好走。挤着眼,仰着脖,腆着肚,胳膊像纸船上的桨划来划去的,腿像上了辐条的电动小狗,顶着风嗷嗷叫着从我们身边擦过。不是拽一下我们这些女生的书包,就是捋我们这些女生的头绳,再不就从脊背后狠推一下,叫人冷不防摔个趔趄什么的,他们就都很高兴了。 他们骑自行车也不好好骑。一辆自行车上架七八个人,横把上坐一个,前梁挤三四个,后座摞两个,沿路还再跳上两个挂后轮的轴上,说是压轴。没跳上的就跟车跑,一直追着要跳。像一嘟噜才刨出来的山药蛋,他们连根连须的挂在自行车上,也嗷嗷叫着擦过我们身边,也拽我们这些女生的书包,也捋我们这些女生的头绳,也从脊背后狠抽一下我们,叫人摔个趔趄……每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女生就瞪直眼紧盯那辆自行车,嘴里吹口气,心里暗暗喊:倒倒倒—— 他们那辆自行车在汽路上七拐八扭,哗啦一下倒了。架在车上的,拖在车后的,也像一嘟噜山药蛋,根须都摘开,滚落得四处都是。尤其冬天下过雪后的晴天。汽路下的雪化了再结冰,上面又覆一层雪。不待我们喊第二个“倒”,他们定然是连人连车都跌了。他们吃了跌,有的滚在汽路上,有的跌进汽路边的沟里,七零八落的。书包撂在汽路上,书包里的书呀本呀,铅笔橡皮三角板圆规这些文具,也散落得四处都是。 恰我们捉马村的素明开着手扶拖拉机才从地送肥回来。他短刷刷的小平头扣着顶帽沿软塌塌的帆布劳动帽,黑豆般圆溜溜的眼目视前方,腰板挺得板直,两只手架在拖拉机长长的把手上。他整个人随拖拉机的空车斗乱颤一气。风像蛇哧溜鼓起他列开怀的帆布劳动装,窜进他的袖管裤管,架得他虚突突的像个草扎的人。 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人的自行车一倒,人跌得七零八落,自行车歪在汽路上,书包呀书呀本呀,铅笔橡皮三角板圆规这些文具又满世界散落。躲是来不急了,只见素明身子一紧,两只手扶一扶把手,一只手用劲往下压,一只手又用劲往上挑,他钻了风的鼓鼓的身也斜斜的抬起,重心落一瓣腚和一只脚上。这个时候,手扶拖拉机通灵一般也顺势翘起半边,一边的轮擦地,一边的轮悬浮,空斗里的小东碎西骨碌碌滚到低处……素明的眼越如黑豆般圆溜溜的,腰直得似一片钢板,两只手凸的凸凹的凹像彩描的解剖图,筋骨分明。他架着手扶拖拉机精准的绕过汽路上跌的人,躺的自行车,散落的书包呀书呀本呀,铅笔橡皮三角板圆规这些文具。我们都揪着心,捂住眼,从手指缝里失惊的往外眊。 待素明和他的手扶拖拉机复了位,他眯着眼斜咧着嘴,用袖管擦擦汗,照例两眼圆睁目视前方,腰板板直,两只手架着拖拉机,虚突突的身板乱颤着,走了。 我家也算和素明家沾了点远亲。他好像大我三四岁,按辈分,该叫我姑。可我不想和他这样的乡村手扶拖拉机手攀亲。凡他开着拖拉机过来,我这个姑都绷着脸,心里却也替他这个侄子捏把汗。 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捂着腚,拐着腿,瘸着脚,捏住鼻,皱着呲眉咧眼的鬼脸,冲着素明手扶拖拉机屁股后冒的黑烟,噢噢乱叫一阵,回头抖抖书本上的灰,用衣裳角擦擦铅笔橡皮三角板圆规的土,往书包里拾东西…… 我们就捂着嘴,一路笑着越过他们。小梅笑得跑不动了,浑身抖得像筛糠,肚子抽得都直不起腰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病得打摆子哩。 开春,小梅突然不笑了,话也少了。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疯跑过我们身边,揪了小梅一股辫上的头绳。也看不出小梅到底生气还是不生气,反正她不笑了,随手拆了另一只辫,嘴里叼着那股红色透明的塑料头绳,一只手在头上拢,另一只手窝在脖子后,握着拢好的头发,三下两下将两股辫合成一股,辫成一根辫。那辫像刷锅刷,撅在她的后脑勺。一路上她都不吭气,问得急了,她翻我一眼,还不吭气。如此两三回以后,小梅干脆辫了个歪辫,斜甩在肩膀上。她早脱了厚笨的棉袄,外面虽还穿了罩棉袄的紫地碎银花竖领布衫,可她将那竖领翻开,露出了枣红色半高圆领毛衣。那枣红色半高圆领毛衣又翻出镶白色麦穗边的粉色假圆领。她歪歪的一条辫擦着那镶白色麦穗边的粉色假圆领,越有一种妖冶的异域丽质了。 汽路两厢是枝枝杈杈的大槐。隆冬一过,大槐杵在晴空里的干枝杈出了米粒般的树芽。小梅仰起头眯眯着眼,她看着那树芽发一会癔症,拖着我往前跑一阵,再立住,圪蹴在汽路边的沟坡上,看才冒的野草芽。看半天,自顾自走了。走了半天,大概想起还有个我,这才回过头,向我摆摆手,埋怨我:七老八十了,不知道走快些? 我噘着嘴蹡蹡朝前走。这回她落后了,又骂我:毛驴,光知道蒙眼走? 弄得我左右不是,可我还和她好。她是留级生。她说她只留一级,可青苗,彩霞她们说她留两级都不止。不管几级吧,反正我和她好。 2 清早下了场雨。雨不大,零零星星湿了地皮。这点雨水,催发了我们太行山上的各种春情。树木的枝条都发了长长的芽,野草也都冒出来了。连语文曹老师都耐不住了。 下午最后一节课,教室门缝那条窄扁的太阳光,像金黄蛇哧溜的尾巴,悄悄抽走了。天像掉色的一大块湿布,淋淋漓漓洇下一团一团的暗青。曹老师拿着教鞭在手心里敲。他敲的乱,我们的心更乱。曹老师有个习惯,下课前要训一通话。他训,有时候不点名,有时候点名。至于点谁不点谁,颇有些抽奖的意思,随机。通常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调皮捣蛋的男生中的几率最高,几乎到每天和每节课一训的地步。训完,曹老师一只眉毛往上吊,一只眉毛往下挣,鼻子抽抽,嘴角翘翘,眼里泛着萤萤的光看住我们。每这个时刻,教室里寂静如空岭。我们身体各路神经也绷得紧紧的。 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验证过,说这个寂静的时间段也就一分钟左右。正常算,一分钟确实不长。我们也知道这是曹老师和我们耍。可不知道怎么的,每这时,我们都像进入一个诡异的漩涡,整个人都往虚幻里急速跌落……又觉得身体失了重,像浮尘飘在黑魆魆的洞里…… 我们就要撑不住了,曹老师压着嗓低低说一声:下课—— 不耍了。 那天,曹老师没有训,突然说了句“下课”,一撂教鞭,咯吱窝夹着教案自管自往教室门口走。我们还有点反应不过来,坐着不敢乱动。大虎,二狗,三猫互相使个眼色,背起书包,脚一蹭一蹭的离开课桌。看看曹老师果真打开教室门,要出去,知道这课是真下了,都像离弦的箭,“嗖嗖嗖”朝教室门口发。 我和小梅也慌忙背书包往门口挤。明天可是礼拜,我们一时一刻都不想在这牢笼般的教室了。这个时候,曹老师突然反转回身,立教室门口,若有所思看着黑板。 大虎早没影了。二狗,三猫他们几个跑得慢的,转头回望着曹老师,略犹豫了犹豫,到底折回来了。一多半没出教室的同学,只好也回来了。 曹老师干咳几声,清清嗓,眯眼扫扫我们,说:明个礼拜,加一样作业—— 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抠鼻子吐舌头做鬼脸。我们女生叹气的叹气,翻眼的翻眼,噘嘴的噘嘴。也还得等他下文。 曹老师可就说了:老顶山—— 这一句捅了马蜂窝,乱巢了。二狗就地翻个筋斗,揪着书包抡几抡,书包就滚出好远。三猫疯了一样在人群里乱踢乱咬。其他男生又是顶拐,又是倒立,再不就举着拳头乱捶。小梅抿着嘴笑。青苗红着脸笑。彩霞腿扭着麻花笑。我自然也高兴,可想着这春游又得和我母亲要钱,惶惶的。 老顶山在我们这个城的东边。冬天,老顶山覆盖了厚厚的雪,像供神的若大个馍馍,白覆覆献在那里,远离了人间的烟火气。这个时候,人是多不去的。只待春暖花开,蛰惊起蛹成蝶,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开始往老顶山去了。 通常,男青年们都仿港台歌星那样,留长长的甩来甩去的偏分头。也一般都备一副塑脂蛤蟆镜。有了这塑脂蛤蟆镜,男青年们时时做一些譬如翘起食指象征性推一推镜梁,扶一扶镜框,亦或哈几下蛤蟆镜,用衣袖仔细擦镜片……这些装饰性的小动作。他们又好像很不经意的吊挂那蛤蟆镜在毛衣领口当央。当然,最好是鸡心领的绛红色毛衣。蛤蟆镜横坠在鸡心领的心尖——那一种风雅就略有体现了。他们穿钉铜扣的牛仔夹克衫,扣不系,衣衫略略敞开,露些胸怀。两片衣衫似旗翼,乘着风猎猎地后飘,呈现那种有点先锋的文艺气质。浅腰紧臀的窄腿牛仔裤,最好浅紧到前裆隆起一团略显的暧昧。他们这就吹着口哨嬉笑,用新词汇互相打一打趣,有所收敛的表示一下解放了的新头脑。 女青年们尤其对男青年们浅腰紧臀的窄腿牛仔裤前裆隆起的那团暧昧,还是很有知觉的。文静傲气的红着双颊,扭脸看住远方,留个羞涩的背影。活泼胆大的暗瞭一下男青年略隆起的前裆,切切私笑一回。 电烫有点没落了。我们这个城大十字的“小香港”“大上海”发廊,已经启用冷烫汽烫这些新的花式烫发技术了。她们的长发大波浪像一股翻花的水瀑,短发小碎卷似盛开的几十成百朵丝菊。时而卷时而直的半烫,似无声的乐韵,流出曼妙的歌。齐眉刘海的倒显得非常文静甚至有点压抑,可阳光下流波闪亮的黑发泄露了她们青春的秘密,诱惑得男青年们目眩眩的,心躁躁的…… 女青年们穿各式化纤格子外衣,长短不一的各式毛料大氅,粗棒针的毛衣外套,或者就是一件夹克牛仔衣……配偏口化纤直筒裤,敞口小喇叭裤,亦或是金属拉链的正口牛仔裤……鞋么,枣红大红深蓝青黑不拘,也多是方口或丁字的半高跟猪皮或人造革的鞋。猪皮刚上过油,那些排列规则的毛皮孔释放出幽怨哀婉的气息,越显出青春于苦短人生中的珍贵。人造革的也上了鞋油,那种人造的光就越脆亮浮夸了。戴蛤蟆镜容易和女流氓一类的角色混淆,故而多不戴。都戴那种能团手心俗称“一把抓”的镂花化纤纱巾。这种纱巾有深入人心的鲜亮,越洗越艳。“一把抓”搭肩绕指,都飘逸逸的。 借了相机。最好是彩色胶卷。还最好男青年怀里斜挎把吉他,偶尔弹一段《冬天里的一把火》,跑了调也关系不大,要的是那种派头。也最好还提个四喇叭双卡录音机,一路放《故乡的云》。那磁带是翻录再翻录的,音质本就不太好,突然叽纽忽哨走了音——带搅了。 女青年们斜挎小小的人造革坤包。坤包里装了面包饼干之类的西式点心和几听健力宝。也可以背水壶。早不背那种老式的行军水壶了。背我们这个城大十字百货商店才上架的那种塑料保温水壶。壶盖黄,壶身绿,壶盖里面的壶口又红,系壶的塑料绳则红绿黄兰各式颜色交缠编织。总之,那只塑料水壶几乎是集这世上鲜亮多彩的色于一体。至于保温效果,总是不能太过于讲究的。 自行车以加重最为常见。骑车出力流汗,不必说,多是男青年了。后头坐车的,男的叭叉双腿,两手一撑跳上后座,或把住骑车人的腰或撒开,都没关系。他们腿微微前屈,一来避免触地造成前行的阻力,二来双腿瞬间伸直,和后车轮成个稳固的三角架,形成紧急防险的落地机制。女的横坐,多是面左,和骑车人形成“丁”字,身体尽量和骑车的男青年保持点矜持傲慢的间距。男青年骑车力道过猛,自行车左右摇摆,后座的女青年随惯性也摇摆起来了。一个不小心,女青年的右胳膊会碰触男青年的后背或腰臀部,其实也只是外层衣衫有点小摩擦。这个难免。碰触也好,摩擦也罢,都轻微,或许还不及野蝶的薄翅扇起的那点风。可男女还是感觉到了,彼此都有了点微妙的情绪也是可能的。 老顶山早踩出条蜿蜒小道。远看,这小道蜿蜒得像犯洪的细河,裹挟了泥沙从山顶泄下来,有几分凶猛。男女青年常偏离了小道,钻进山腰的松树林。松林里就叽叽咕咕的,不知道的以为是双栖双飞的鸟。 老顶山的半山腰,有许多卧石。大的有三五间房屋大,小的似个小草蒲。男女青年在卧石上追逐嬉笑。女青年互相换穿衣裳,“一把抓”搭在肩上,捏在手里,或立或坐,或枕臂仰卧,或俯身翘腿,各种娇媚。男青年脖子上挂着海鸥相机,围着她们。这个笑说:头,头,扬上去一点—— 那个提醒:手,手,托住点下巴—— 照相的喊:笑笑,再笑笑,别动,别动,好,好,三二一—— 山风吹过来,只听咔嚓一声,照了。 那年春天,男女青年这一种浪漫奔放的风姿,我们看在眼里,初怀的一点点心思,发了酵,虚突突的喧起来了。以往,我们班也集体去老顶山春游,男女同学也相邀上过老顶山。我们去老顶山,和大人要些零花钱,买些话梅糖呀,山楂片呀,一包香甜饼干呀,一听健力宝呀这些。我们一路吃一路走。不到山脚,我们吃完了。吃完,我们就耍。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顶拐的,翻筋斗的,弹玻璃球的,拍烟盒的,再不打一回架,再不睡一回觉。我们一干女生用塑料绳翻花,咬耳朵说话,互相辫一回辫,最多在路塄边摘几朵野花。耍乏,我们都不想上了。老顶山就是个山嘛。 可那年,也不知怎么,但凡敢说老顶山,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就噢噢的乱。我们一干女生要不面红耳赤的低下头,要不捂住嘴嗤嗤笑,再不翻白眼,再不身扭麻花羞丑丑的。明面似要撇清,私下却都很愿意讨论老顶山这个话题了。 3 一早,校门口集合。 曹老师寥寥几根胡须不见了,下巴留了粗糙的浅青色,像蟾蜍的皮。男生们也都打理了头面。大虎的面皮白净净,脖子耳根黑污污,像戴了个面罩。二狗三猫竟还理了发,精神得都很有些不像了。女生们的出场都很隆重,个个光亮白净,明眼皓齿,粉润润的脸。有的女生脑后扎马尾辫,这也是目下我们这个城比较时兴的发式。几个女生学小梅,梳了根歪歪的辫。穿着不必说,都下功夫尽量穿出成熟的那一种风致:卡腰衣裳,裤缝笔直的华达呢裤,配白尼龙袜的猪皮方口皮鞋——这些行头都是借穿或者偷穿的。衣裳顺腰卡出一弯月牙似的凹线,距她们的腰依然有一个宽度。华达呢裤过于宽长,裤缝折得像断蛇。猪皮方口皮鞋基本都不合脚,大的像拖鞋,小的夹着脚。我母亲倒是拿出她那双黑猪皮方口鞋叫我穿,那鞋头已经磨糙了,后脚跟裂了缝,如何穿的出? 小梅照例穿了紫地碎银花竖领布衫,照例竖领翻开,露出枣红半高圆领毛衣。那枣红半高圆领毛衣翻出淡紫镶荷花白边的假方领。歪歪的一条辫照例斜刷在她的肩上。她穿了“半高跟”那双枣红半高跟牛皮鞋,一下就挺拔了。 春日和暖。无风无云。小梅脸上却蒙了粉色的“一把抓”。“一把抓”上镂的牡丹花覆住她红红的脸,越衬的她半截脖颈粉嫩嫩的。她手提白色透明薄如纸皮的袋子。 小梅说:人家大城市现如今都兴提这样的塑料袋—— 花剌剌的糖健力宝,两个国光苹果挤在塑料袋子里,像打了沙暗的蜡,借着那薄薄的塑料衣闪烁着迷幻的光。我第一次见这种叫塑料袋的东西,由不得对制造这新物件的新技术发一种惊叹。 曹老师也不以为是坏事,弯腰嗡在塑料袋上瞅瞅,又用指头戳几下,点点头,算作认可。 青苗,彩霞起先嗤着鼻,斜着眼,离小梅远远的,作出藐视那个塑料袋的样,如今见曹老师认可了,也赶紧学着,弯腰嗡在塑料袋上瞅瞅,指头戳戳,点点头,也认可了。 农科所的试验田是青雾雾一片麦苗。麦苗细长的青叶上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小梅蹲下身,用手心接了一滴露珠,托着走。过铁路口,一个偌大的火车头,喷着偌大一股蒸汽,咣当咣当开过来,后面挂着十几节运煤车皮。小梅拽住我,立铁路口,看着运煤的火车消失在蜿蜒的铁路尽头。 老顶山下的村,叫鸭儿堰。正会。 牵牛马赶猪羊的山民,吆吆喝喝的来。挑担里扎着猪娃鸡娃的山民,又唧唧咕咕的去。村中央的窄巷摊着满漾漾的卖铺。吃铺不用说,蒸煮煎炸烧烤的泥炉灶隔不远就一个。吹糖人的,爆米花的,剃头的,稻草插糖葫芦的也都不缺。另有日用杂货,估衣布匹等摊铺,也有铁匠铺,疙炉锅摊……新簇簇的女子,体面面的后生,霸着嗓的婆娘,举着吃的的小孩,人腿里钻的野狗,短墙上飞的草鸡,窜房檐的狸猫,叫喳喳的喜鹊,刮噪噪的麻雀…… 独没见和这鸭儿堰村名有关联的鸭儿。 曹老师紧着喊:跟紧,跟紧,赶紧跟紧—— 哪有人听。 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早没影了。 小梅拽着我,钻进人堆。看骟猪。骟猪的婆娘剪发头,霓彩服,解放鞋,一只眼斜睨着睃我们,一只眼看着山,手捉猪娃早动作起来。猪娃嗷嗷叫着挣脱,声音似冰冷的锥子,尖锐的刺过喧腾的村巷。小梅一只手捂着眼从指缝里瞄,一只手的指甲早切进我的手心,切得生疼生疼的。骟猪的婆娘不慌不忙剌口子,掏卵,骟卵,捏住泉眼一样汩汩冒血的刀口,弯腰抓把黄土猛一扣,血就止了…… 再遇货担。针头线脑的挑子铺摆得红花柳绿。我们各扯了两根红塑料头绳,缠在中指假当金镏子。又来个卖鸡娃的。染了红顶心绿顶心的来杭小鸡娃摊在偌大笸箩里。小梅喜得什么似的,挨个摸小鸡娃的顶心。卖鸡娃的粗大爆筋的手覆住笸篮,说:才出一天的鸡娃儿,不买不能摸哈—— 村口,坐东朝西个戏台。几个后生脑门上冒着汗,光了膀,露出精瘦又充满朝气的古铜色身板,越衬出那青灰戏台的旧拙了。他们忙着搭银幕,胸前,两臂和脊背的肌肉群在阳光下时而急时而缓的跑动,像潜着水的大小鱼儿。小梅脸红红的朝着我,眼却眊着后生们古铜色的脊梁。我悄悄扯她的袖。她突然回过神来,捂着嘴笑。 曹老师早等在戏台旁了。好大一会儿,大虎,二狗,三猫几个人慢慢聚拢来。他们和搭银幕的后生打听。回来学说晚夕要放《少林寺》。可如今太阳偏东,正午还不到。都懊恼。这时候,我眊见个年轻人,背对我们,也立在戏台前。他高高瘦瘦的,肩上斜挂个黑色人造革包。他仰着头只顾看那戏台,长长的偏分头在风里飘,一身深蓝的腈纶运动衣。那种运动衣才在我们这个城兴起。城的大十字百货商店有卖。翻领的边,衣袖和裤的外侧都镶两道寸把宽的白边。因腈纶料软,贴身粘着,显山露水的。他这样的打扮,比那些带蛤蟆镜,穿牛仔衣裤的年轻人,更多了许多新意。 我左右眊眊,未见别人,心知他一人上这老顶山来的,耳根突然烧起来了。 七等八等的,人总算齐了。顺那条蜿蜒的路,我们登老顶山。登着登着,小梅突然“哎呀——”一声。她脸色煞白,跺脚四处张寻。原来她蒙脸的“一把抓”和提在手里的塑料袋都不见了。 她巴巴的看着我说:塑料袋好说,“一把抓”怎办? 原来她偷“半高跟”的“一把抓”了。 也顾不得曹老师和同学们了,我和小梅返原路寻。一路也有男女青年三三两两过来过去,我们就看女青年扎在脖上和拖在手里的“一把抓”,倒都不像小梅的。 返到鸭儿堰村口,近中午。会大喧起来。一拨一拨的山民顺山路往村里拥。小梅一脸灰灰的。我把我带的香甜饼干拿出来。小梅也吃不到心上,说:你憋不? 我说:憋吧—— 又寻茅家。村口倒有一个,石板砌的围墙。我们钻进去,眼见那大蛐拖银长尾巴,小蛐嫩肥身段,爬的爬,滚的滚,四处都是。石板墙只砌到小腰处,稍有动作外面都看得清楚。我们只好退出,就近爬上一堵塄。塄往上都是梯田。麦苗长得没过脚腕了。我们穿过麦陇。小梅虾腰捂肚扭屁股,跑在前。我紧跟小梅,土坷垃钻了一鞋,也顾不上倒。我们上了两个塄,往一颗粗大的旱柳处去。 小梅着急忙慌揪开裤带,背着老旱柳唰啦蹲下,露出雪白的腚。我也背身解带,要蹲,却见小梅的脸憋得红罡罡的,嘴张成个洞,铜锣大一双眼死板板的定住了。没等我反应,她的脸又蜡黄黄的,嘴唇哆嗦,腚下像安个弹簧,腾的一弹老高,手却哆嗦着提不起裤。裤提起,又系不住裤带…… 就撇见前面一个男的,相隔我们丈把远,衣裳穿得正正当当,连领口的扣都系得严谨谨,嘴脸却邪性。他两只手在裤裆口拿拿捏捏的。他的裤口露出红罡罡一点内色,吊不清不楚一坨货。他两只手又用力拿捏那坨货,有些挣扎难忍的意思。我由不得往前挪挪,待要眯眼细看,小梅拖着我就往塄下跳。 连滚带爬跳下几个塄,着急忙慌冲到村口。见了人,小梅才甩开我的手,喘着气,捂住心口,着恼得厉害,又不说话,冲我翻白眼。 到此时,我也有些醒悟,浑身像泼了汽油,烧灼得厉害。脸和耳朵似在火上烤,感觉全身冒焦烟……我有点眩晕,周身的血脉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喷发和翻腾。我很清楚看见小梅脸上浅麻的蝇屎点,可又觉得和她的时间空间交错,不在一个点上了。不知道我远,还是小梅远,反正是远…… 偏这时又和人撞个满怀。这人一身深蓝腈纶运动衣,衣袖和裤外侧镶两道寸把宽白边。山风吹着他运动衣的翻领,覆住他少半个脸。没来及细看他的脸,却撞见他高高的喉结,情知是早先戏台下那个年轻人。我赶紧翻转身,耳根越像笼着好大一盆碳火,烧得罡罡的。 偏偏大虎又横在羊肠道上,双手捂成个喇叭,朝山下的我们喊:快些呗—— 这时候,我的肩又叫人点了下,有人问:寻这个么—— 素明立我背后,手捏小梅的“一把抓”,头上冒出滢滢的汗珠,脸红红的,像是跑着赶过来的。他大约来赶会,穿得齐整整的。我也才发现他这一拾掇,脸上带了不少英俊之气,有个青年的模样样了。 我拽过“一把抓”,黑着脸训素明:你凑什么热闹,怎不早些拿来呀—— 拽着小梅往山上走。 我们渐登渐高。近处山石险峻,松涛惯耳,鸟鸣声似汽锅爆的玉米花,落得四处都是。松林隙间,可见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背影。偶尔风过,也听见了他们说话,只是那说话声像断了的蛛丝,虚飘飘的。 我和小梅立在山石上,迎风朝山下看。近的村庄微缩得小小的,仿佛可以托在掌心。远处的城越小得可爱。楼像积木,路像皮筋,烟囱像一根点着的香烟。一条银亮的色带像断开的镯子绕住半个城,那应该是漳河了…… 4 老顶山春游回来,发生了一件事。 也是自习课。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文的撕作业本叠飞机蛤蟆,教室后小块空地上弹玻璃球,拍烟盒纸叠什么的。武的弹弓弹粉笔头,塑料手枪乱射塑料霰弹,用黑板擦或者教鞭棍打斗什么的。半文半武的走道顶拐,练“二指禅”什么的。女生们说的说笑的笑,吃的吃喝的喝,互相辫辫,翻花,拍手什么的。 一时反乱得厉害。 趁着这乱劲,小梅的头倒在课桌上,一只胳膊捂着一只手写着。我的头篷住课桌,两只胳膊护着腿上的红塑料皮的手抄本。那段时间,我很偏爱于这嘈杂纷乱中偷享手抄本里脸红耳热的男女情事。猛然间,我的右肋叫大虎的铅笔头狠劲笃了一下。周围的嘈杂声也如急雷速疾闪去。空寂像水瞬间漫袭过来。我慌慌收拾手抄本,抬头观望,早见曹老师扑风鸡一般旋进门,手像拾豆,“叭叭叭”从几个男女生手里桌兜里没收过魔方,水哨子,玻璃球,连环小画书,弹弓石子,塑料手枪,塑料霰弹,烟盒纸叠什么的。小梅胳膊下压的小纸条什么的也叫拽走了。 亏大虎,我的手抄本压腚底了。 曹老师没收的魔方,水哨子,玻璃球,连环小画书,弹弓石子,塑料手枪,塑料霰弹,烟盒纸叠什么的,撂在讲桌上。他在教室里来来回回走,瞪一双风火眼,手里的教鞭在另一只手心敲得哒哒的。曹老师穿双露指头的解放球鞋,红尼龙袜。他的一只鞋带拖拉着,一只鞋底后跟沾了半片枯叶。他好像才从建筑工地下来,一脚的泥灰印。那泥灰在他脚下又掀起一阵暗风。 眼瞅曹老师一只脚踏上讲台,可他突然又缩回来。我们的心都悬起来,屏气收声,目光聚焦在曹老师的脚上。他沾了片枯叶的脚在另一只脚的脚面蹭蹭,半片枯叶忽悠悠的扇。他的两只脚终于踏上讲台。教室里的缓气声像暗流涌来荡去的。就见曹老师教鞭一横,将撂了一讲桌的魔方,水哨子,玻璃球,连环小画书,弹弓石子,塑料手枪,塑料霰弹,烟盒纸叠,小纸条什么的一推,清了两声嗓。 惯常曹老师没收了这些,干清两声,面上若不很严厉,就可以下课了。 大虎手抬起,准备收拾书包了。我扎扎攮攮坐手抄本的腚,到此时也才安稳些了,手也稍稍往下走了一走,趁势抽走腚下的手抄本。可这时,曹老师突然盯住讲桌的角,眼像两只萤火虫,发出莹莹的光。他缓缓放下教鞭,扒开那堆没收的东西,食指拇指轻轻一捏,捏起个折角的小纸条。 夕阳透过云层穿过来,有点模糊,经门缝一夹,像挤伤了,成窄窄的一条灰黄色伤疤了。曹老师捏着纸条一角,像捏着灰蛾的翅,慢慢往起提。提过胸,将那纸条放到门缝的窄光里,对着纸条透视一番,甩几甩,鼓起瘪瘪的嘴,吹一吹。另一手的指头依次张成扇形,拇指和食指圈成个小圈再略略一松,就势轻轻弹那纸条。纸条疼得抖了几抖。 高年级偷偷传纸条的事,我听小梅说的。小梅说的时候,每个字好像透过细细的牙缝钻出来,听得人心里痒痒的。她红洳洳的唇抿成薄薄一道粉线,似饱满丰润的玫瑰花苞,诱惑得人想做点什么才好。高年级的男女擦过身,小梅会突然使个眼色,抿嘴做些鬼惑的提示。我就知道这男或女,和传说中的纸条有瓜葛了。 我也私下琢磨纸条的事,想着不拘从那浅绿条格的数学本或是粉红方格的作文本,亦或是油印公文纸背面制成的草算本上撕下一角,写下略带些暗语的表白,叠成个三角或是四方的纸条。纸条的首尾两端像蜻蜓翘起的尾蝶,飞飞的在男女手上传来传去,也实在惊艳。 那天,我们都屏住气,盯着那薄飞飞的纸条,面上羞涩,心里忐忑,却又都暗暗期待。曹老师几乎用慢动作展开了纸条。纸条其实也就一指宽,是个小小的不规则三角形,有犬牙一般手撕的痕迹。从我这里看,隐约带些绿洇洇的烟气,该是从算术本撕下来的。 曹老师将纸条嗡在鼻尖上,眯眼盯住纸条看一阵,眼翻过镜框朝下瞄住我们。我们女生就倒下一大片。我胳膊架在课桌上,头篷在胳膊上,袖子遮脸,耳朵听动静。 曹老师干咳一阵。大虎,二狗,三猫一干男生随曹老师干咳,嗓眼冒出怪怪的笑,弄得人身上冷飕飕的。 曹老师这就念:大虎—— 我心一紧,耳根像吹起一笼碳火,立时烧得头脑有些发昏。曹老师的声音像在千里之外,又远又细还漂浮不定,可偏又清清楚楚。他念:你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 教室静雅雅的,像针管抽干了空气,憋得难受。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反应过来,哄堂大笑了。我也赶紧抬头,很愿意撇清那样咕咕笑几下,眊眊大虎。 大虎的脸像张粉莲纸,煞白。 那个纸条像一张封条,制住了大虎。他见天黑封着脸,有树就躲树影下,没树就溜墙跟。写字,两只手搁他那一厢的课桌角,低眉顺眼腾出一大块空桌,好像很欠了我。倒是二狗,像个新封的猴王,活跃了。 依二狗自己的说法,他实在不喜英语这一门鸟课——其实,他哪门课都不喜的。赵老师来,他就喜了。以后,他竟还考了我们这里师专的英语系,算个大学生了。 英语赵老师是来我们太行中学实习的大学生。赵老师长得高高大大,留着遮住眉毛的半长头发,窄条脸,浓眉毛双眼皮,高鼻阔嘴,长脖长胳膊长腿的。 二狗说赵老师:长得有那么点仿生—— 这也是二狗说过的最有哲学高度的话了。 赵老师穿烟灰色的咔叽西装,白的确良衬衣打猩红尼龙领带,一只裤腿半卷,另一只裤腿扫地,脚上一双蓝边白网鞋。他进门就往讲台跳,一跳就跳脱了,讲台的台阶绊了他一下,他倒是未倒,跌跌撞撞上了讲台。我们以为他上了讲台就好了,谁知他脚未刹住,又从讲台的另一端趔趄下来,头往下栽,两条细胳膊后翻,屁股往上撅,腿往后撂,眼看要撞墙跟盘的那炉泥火了,他翻着白眼珠突然刹住了。 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姓赵。 他刹住,急切翻开手里的花名册,喘着气开始点名。我们不知道怎回事,慌着应答。他喘着气点完名,又喘着气叫我们翻开课本。 我们的讲桌是半圆形的。朝外的圆弧是一拃宽枣红竖木条圈的,正中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显镶,黄色,也用木条拼的,每个角有棱突。这些棱突又鼓起个小型的五角星。因着时间久了,讲桌的枣红色和五角星的黄色都斑驳驳的。三两条枣红的竖木条也空了。 他露在讲桌上的半个身子还立得直杵杵的,只是那讲桌洞下有窸窸窣窣的响动。我们透过空隙,见他的两条腿打摆子。他大概想控制又控制不了,就把两条腿顶到讲桌洞的撑条上。窸窸窣窣的声变“哒哒哒哒”的声了,听着有点像机关枪远渺渺的扫过来。 这课上的他像长跑,他一直喘气不说,大约领带也系得紧,脸涨得红罡罡的,头上冒豆大的汗珠。这个时候,教室门开了。曹老师立门口,“半高跟”立在曹老师边。他们俩在逆光里,脸不清不楚的。曹老师的身架还可,“半高跟”的身架冒着遏制不住的怒气,腾腾的。 “半高跟”自然是因为小梅给大虎写了那张纸条,来学校的。 “半高跟”“蹡蹡蹡”闯进来,拽小梅。小梅一甩“半高跟”的胳膊,倒也没吭气,立起身默默往外走。曹老师这个时候还立门口。 赵老师——这个时候,我们也还不知道他姓赵——突然就从讲台上跳下来,横在“半高跟”前,说:请问,你是谁?怎能随便带我的—— 顿一顿,咽口唾沫。他的喉结上下滚几下,才又接住刚才话茬,说:我们学生—— “半高跟”愣怔一下,朝门口看。曹老师就进来了,说:小赵小赵—— 这会儿,我们知道他姓赵了。 5 我们太行中学校园后一片小树林,都是杨树苗。平日,杨树苗都直杵杵的。风动,杨树苗随风摆起,翻着背带鱼白短茸刺的叶,唰啦啦响,像伏了刀斧手,萧森森的。 紧挨小树林,是我们太行中学的厕所。厕所露天。青砖砌的门户。门户两边外墙分别画斗大两个黑圈。圈里套“男”“女”两字。男左女右。拐过门户,各去各所。内里斜纹青石条铺坑。坑上,男女间隔一堵薄墙,大小响动都听得真切。坑下则互通。冬天,坑里也是滴水成冰的景象。夏天,雨水注入,坑面清澈如水银灌的镜面,倒影楚楚。蹲下能见莹莹蓝天。立起一望,放远青乌乌的太行山峦。 小树林和厕所一墙之隔是庄稼地。这原是我们捉马村素明家包产到户的。素明家种清一色玉茭,据说是卖玉茭做饲料。我们捉马村人都说,他家挣钱挣痛了。后来土地越来越少,就不给素明家包了,分给各家做自留地。我家也分了二分。素明家也在那里留了几分。 地少了,各家种了各种杂色的庄稼,供自己吃鲜。玉米,茭荞,小麦,谷都有。有那勤谨的,陇间也还套了扁豆,豇豆,南瓜等各式耐旱菜蔬。上地的人杂了,我们太行中学的这个厕所,难免也就有些不三不四的诡惑传说了——这是我后来的判断。 据说,一对男女从外墙翻进来,来小树林上过吊。厕所也出事。据说,坑里也浮过一两个未成的婴孩,白嫩嫩的性别都可辨出来了。据说,冬天,耍流氓的立坑下女的一侧冰峰上,拿小棍往上捅。还据说,也是女的一侧,耍流氓的从墙眼往里眊,爬墙头朝里看—— 这些据说传得我们女生心里发毛,提心吊胆的,倒养得一样毛病:有个动静就骚动。 那次,曹老师拖堂,我们下课迟了,都拥拥挤挤的在女门户这厢排队。小梅有些急,两只手捂肚,两条腿一拐两拐的。她想插个队,青苗和彩霞排在前面,故意挡着。小梅和我使个眼色,意思要我来引青苗和彩霞,她乘机闯。这关口,就听里面一声惊呼,呼啦一下几个女生全跑出来了,有的兜裤,有的兜鞋,慌得什么似的。我们外面等的一看不对,也紧着一边惊呼一边跑。我,小梅,青苗,彩霞几个早磕磕绊绊滚跌在地…… 隔壁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打那边的门户钻出来,头发竖起,眉眼圆睁,捏着拳头朝女的这边看,都准备翻墙跳进去逮了。结果一问,是只喜蛛蛛吊了股丝,落下来了。 还来说说赵老师这个人。 每上课,赵老师都烟灰色咔叽西装,白的确良衬衣,猩红尼龙领带,一双蓝边白网鞋。他进教室门也还往讲台跳。以后,他一跳就跳上了讲台,落地还稳。他上课也还好,一边讲一边做些金鸡独立,螳螂捕蝉,另有一些说不来不过幅度不很大的武打动作。他也喜欢画,黑板上画各种格斗招式。他讲课,不管什么总要扯上打。下课,他二踢脚,鹞子翻身的来几下幅度大得夸张的招式。教室比划不下,就跑教室外比划。 只要没课,赵老师总去小树林。他头上裹的蓝墨水写“格斗”的白布,在脑后扎成蝴蝶的翅状。那“格斗”二字贴他额头上,有些像老虎胎带的“王”,很有雄风。他穿腈纶运动衣。深蓝色,翻领边,衣袖和裤的外侧都镶两道寸把宽的白边。因料软,贴身粘着。后来,我们知道那是带了静电的缘故。赵老师穿带了静电的深蓝腈纶运动衣。运动衣贴着他的身。他的身就显山露水了。到此时我不说也知道,赵老师是我们春游那天在老顶山下鸭儿堰看戏台的那个年轻人了。赵老师应该也认出了我。他点我名,很注意的看看我,眼里似乎很有些暗示。 我们班女生都跑去小树林看赵老师,笑得嗤嗤的。尤其青苗和彩霞,笑得颠颠倒倒。她们捂着嘴,可那笑声越漏得厉害,尖忸忸的像无数个小小的电动锥,扑扑的抖擞着往小树林钻。小梅不笑,我也不笑。 有时候,赵老师在小树林里大声朗读英语。我们都没见过外国人,可高低觉得他读得比外国人要好。有人就说了,说赵老师人家要考研究生哩。我们越觉得他比外国人好了。他读乏了,空手打拳,猴不猴,鹰不鹰的样,却好。有时候,他戴两只枣红皮手套,打黑狗头样的吊锤。那吊锤挂在树杈上,叫他打得急速的摆来摆去,更像个黑狗头了。他说那手套是拳击手套,那黑狗头样的吊锤是小沙袋,都是他自制的。他上课给我们讲了他自制拳击手套和小沙袋的经过。他说他拆了一个红色人造革包,一个黑色人造革皮包。红的绞了手套,黑的绞了小沙袋。小沙袋好说,用线绳缝成个吊锤样。手套就难了,不过总算制成个套了。他又掏了棉衣里的棉花,塞进手套和沙袋,当瓤。封口。小沙袋口处缀股解放绳—— 全用英语。有的我们能听懂,有的听不懂。他一比划,我们懂了。 他叫我们传看他的沙袋和拳击手套。沙袋也就那样。拳击手套其实和我们冬天的棉手套差不多,四指一套,旁边叉出根拇指。不过,他的拳击手套外侧垫了厚厚的棉,里几乎没垫,自动弯成个拳头样,手进去越蜷成个拳头了。很得力道。手套的里小,背宽,他在里背的衔接处扎了细细的花褶,又用的是白线绳。针脚虽有些凌乱,那白线绳扎枣红人造革很有个俏模样。我们传看。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还戴着打了几下。 赵老师还叫我们用英语表述我们的感受。 我第一次体悟到,这世上有一样生活,是之于生活之上的。 二狗,三猫一干男生都跟了赵老师。大虎起先还落寞寞的,渐渐观望,渐渐靠近,也跟了。赵老师他们几个实习生,都只带一个班的课。这一来,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就垄断了赵老师,其他班有想跟赵老师的,二狗三猫他们不许,就进不来。如此,其他班的就来走二狗三猫他们的后门。二狗三猫他们就都跩起来了。 课间或放学,他们都往小树林跑。都买了腈纶运动衣。没有买的也都借上了。有的深蓝,有的大红。他们的运动衣自然也都带了很多静电,贴身粘着。那身也都显山露水的,却肥的肥,瘦的瘦,不如赵老师看着好。也都是白网鞋。头上都裹条白布,两三寸宽。布条前或红或蓝的墨水写“格斗”二字,学着赵老师后面扎成蝴蝶的翅。一出汗,头上墨水写的“格斗”,字都晕了,脸也红红蓝蓝的。他们有扑有剪,有摔有打,有踢有蹬,打得不亦乐乎。 他们在小树脑上挂了面三角白旗,大概就布,也就两三尺长宽。也用墨水,旗边是蓝色犬牙状花边,中央“格斗”二字红色。小树林湿气重,加上雨水露水什么的,旗上那“格斗”二字也有些晕,倒像专意描了花式的边,有些立体和装饰感。 我们课间往那边跑的次数多了。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都说去蹲“坑”。我们一干女生也说去蹲“坑”。曹老师也没办法。大虎,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是借着课间那一会儿功夫,进小树林练。我们一干女生去看。 小梅看得最多,动不动就去。 小树林的鬼惑气早没了。 “半高跟”上回来学校一遭,叫小梅向曹老师保了证,以后再不写纸条了。曹老师也就不追究了。大虎他爸没来校,可那几天大虎的腿一拐一拐的,我们就知道大虎他爸因纸条的事,吊他房梁上打了。据说大虎他爸是部队炊事排老兵,行军能扛五口大铁锅,收拾大虎自然不在话下。大虎还能走路,估计他爸手下很留情了。 二狗,三猫他们一干男生一来碍于大虎的面,二来忙着格斗,偶尔发发赖,打几声口哨嗷嗷叫几下,扮着鬼脸喊两声:你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你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 每这个时候,大虎冷着脸,翻着白眼,从我们身边急速擦过。小梅噘着嘴,手指头绕着辫,眼里盈盈的泛着泪花,眊着大虎的背影。她又怕我看见,脸背过去,影儿在汽路斑驳的树影间拖出一道长悠悠的恨。这是赵老师还未来的时候。 自赵老师来,小梅上课不能专心了。除曹老师的课,她都举手请假,说要上厕所,虾腰捂肚不说,还一脸急切难忍的样,我们看着都替她急,别说老师了。 这大概是她表演才能的初露。 她跟我说她听说了,北京有个电影学院,她想考,想成影视歌三栖女明星,红透两岸三地。她这样说了,我脑子里就想着她像麻雀那样,支愣着两只细爪,忽扇着两片单薄翅膀,立在三根小树杈摇晃晃的,也着实替她忧愁。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ngyedana.com/qydpz/5175.html
- 上一篇文章: 史上最全中药歌诀,全在这了,千万药店人已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