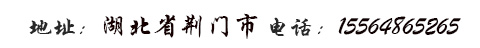高考前的爱情下
|
写在前面: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喜欢的人也刚好喜欢你。 敌营十八年 作者:丁一达 (四) 孟晓微回来我们关系比从前稍好,但也没那天晚上的无拘无束。见了我算是敛了几分气势,多了些和善,毕竟我也算知道了她老底。也做好了她恢复自信就继续从前那种傲慢的准备,情绪是一时的事,性格难得变化,我也只是赶上了趟听了一肚子苦水,可不敢就此以朋友自居。可是日子一久发现孟晓微是真的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有一次还塞了粒糖给我,放在从前真是不敢想象。心里渐渐有些高兴,每次发现她对别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还真有些得意。那天和何北北在路上碰见她,我们对了一眼她就把目光闪开了,我马上意识到她不想和何北北打招呼,就也没做声走了过去。等她走远何北北鼻子一哼,说:“孟晓微真的不招人喜欢。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想人家就是自恋你何北北也没资格说啊,就顶回去说:“人家有那个条件,轮不到咱们说。”何北北有点恼说许愚你没看见刚刚她那意思,就是不想理咱们哪。我心里暗暗说,不理你活该,指不定理谁呢。 孟晓微生日那天放了块蛋糕在我桌上,我一回教室余可可就嘟嘴说是孟晓微给的。我顺着她指的地方看去,孟晓微在座位上分蛋糕。胡楠接过刀具说要切块大的,孟晓微就放下东西四处看,一看我们就对视了一眼,我刚想举起蛋糕谢一句,她眼睛就闪开了。晚自习下了课她走过我们这边说,余可可你没吃蛋糕吗?余可可一脸疑惑说吃了啊。她指指狼吞虎咽的我问怎么他也有呢,余可可说你不是给了我们两块嘛。她也不和我说话就走了,余可可和我嘟嚷说明明她自己放了两块在你桌上,一块能不是给你的嘛。想想觉得孟晓微可能不太好意思,蛋糕不大分的人少,给我吧觉得关系没那么好,不给吧也不太好,丢两块到我桌上看我造化,怕我觉得是特地给我的,还过来敲打一下,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孟晓微不大想显得对我有什么特别,我也就配合,你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就会示好什么时候就会板脸,总之是变化无常,我告诉自己要平常心,但有的时候情绪还是被她牵着走。我想来想去觉得孟晓微其实挺不错,比起原来好了不只一倍,觉得自己要求别人就是过分了,再说是什么关系,聊过一回觉得就是朋友?一厢情愿吧。也就不去理会她的阴晴不定。 毛奇下了第一节课过来喊我接电话,二叔电话里头说奶奶体检有点情况,医院去了。清明他就直接来接我,不回奶奶家了。二叔口气轻松,电话里也就没细问。挂了电话毛奇要我坐下谈,说了些勉励的话,尤其要我不生杂念,说要主一无适。上次跌得那么惨,大步迈向退步,能不是心思出了问题?原来觉得毛奇上纲上线,后来觉得可能确实要到心思上去找根子,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乱想间想到孟晓微,自己都吃了一惊,直摇头,毛奇问你摇什么呢,我脸都红了。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翻来覆去想自己对孟晓微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感性上也没有,理智上也不可能,被毛奇一说心思自己乱了阵脚,连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人家都搞不清了,出办公室我就抽了自己两下。下午放假没打算回家,收拾东西打算和吴准一起去吃饭,孟晓微背着包走过问:“不回去?”我嗯嗯应着,她也没说什么。 吃完饭就和吴准去操场散步,暮色低垂,我听着他踢石子。我说,解放一下思想?块垒都成山了。他狠狠一踢,说他妈真不是人受的,讲自己看书被毛奇批了一顿,这可就给少的那些分数找到了娘家,毛奇讲他心思杂,浮得很。“别思考,许愚,他就觉得你是机器了你就不浮了。”吴准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他们师生相得,今天是说气话。我叹口气,他接着说:“你看在前面的女生,还批判思维,杜森林说不准问就不问,拿了点分就以为真懂了。”讲着讲着他笑起来,说:“拿点分就是真懂啊!就是真懂啊!”我笑笑,说,还吾侪所学关天意呢,那些女生看我们不是笑话?走了两圈吴准平静了些,也不再接我的牢骚话,只是听。我说现在面上鼓励思考,你真要提问还被骂,道理何在?吴准冷笑两声,你也别怪高三没道理,其实是哪都没道理,或者说,我们以为的道理都是狗屁道理。我心下一沉,觉得不是滋味,说你这说的也是牢骚话。他冷笑着说,牢骚?我平和得很。吴准说,成绩是道理,钱是道理权是道理,手段是道理,规则是殉道者的自我安慰和既得利益者的防御工事,潜规则才是真规则。我说要这么讲也太悲观了,照你说做个好人是做个傻子,他一拍巴掌说对了,就是他妈傻子。他说,谁说你没才华,咱们一定揍他,但你也知道不能和贾谊和苏轼比吧,五百年一个的天才又如何?还要怎么少年得志,最后什么结局,有道理吗?十月革命知道谁指挥?托洛茨基!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几个,你说不是大才?最后被斯大砍掉脑袋,他斯大林不守规则嘛,出盘外招,蒋介石不也是?拿你说的道理去审视他们,没一个有道理。我把手攥紧打出去,话也是这么个话,真要去信也不容易啊。吴准叹口气,想要做番大事,又没那个性格,要你有的事能下得去手?说到底我们懦弱啊。吴准接着说,我原先也觉着这样想不是个事,初中的时候能写两笔文章得意得很,老师面上倒是很欣赏,有什么名额指标从没给过我,就是成绩不行,你说你愿意一辈子叫人当摆设?我就横了心,没日没夜地做题刷题,我哭啊,文章就是狗屁,夸你有才华也就夸夸罢了,什么东西都要拿到手才是真的。他骨节捏得出声。他说,别求别人理解你,要就要别人只能远远地看着你,你踩在他们头顶的时候你就不用别人理解了,人人都会知道你是谁,实力就是最大的现实。古往今来想想没有什么变化,原始社会看身体素质,奴隶社会看你的头衔你的权力,现在看财富,我们看成绩,都他妈是一个东西,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是最真最真的规则。 这些话从吴准口里说出来我五味陈杂。没有人知道他经历过怎样的挣扎换来今天的洞破,我不知道该替他悲哀还是高兴。毛主席讲,枪杆子里出政权,真是真的不能再真,对的不能再对。这么多年我都不忍心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好像每次掀开现实的一角,自己的心就要被剜去一块,但不掀开就会有更少的伤害?那些纵容自己在琐碎情感里痛苦地、欢乐地享受的时刻,那些想入非非在太虚环境里沉醉的时刻,与接踵而来的现实所形成的剧烈反差,难到就不是插进心尖的箭头与倒刺?像吴准那样,掀开帷幕去正视,俯下身子趟过泥沙荆棘,心就已经结了一层硬壳,所以能旁若无人地向前,愈向前愈享受,他说,你站在高处时没人能看到你身上的泥。我知道吴准的想法。那些他激昂动情的演讲,并不是假话。他在讲台上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历劫难的超脱是轻佻的,惟有确立向外的人生向度,将自我实现融入进更博大的东西,我们才有战斗与历经劫难的力量。”他在说出那些话时带有深深的蔑视与自得,他已经懂得家国天下不是自我陶醉,而是要在险峻残酷的生活里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因为情怀从来是一种奢侈品,没有血路通向的世俗成功,消费情怀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天下是终极目标也是前进动力,为了不让它流失、泛于空疏,他再没有写过诗。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准已经彻底与从前的自我做了割裂。我去过他家,书的洪水肆虐,没有一处容脚的地方,那么大一幢房子活脱脱被他改成了书店。卧室床头放着一尊纳尔逊像,莎士比亚收到柜子里头,书架上矗着年斯诺为毛泽东拍的那副半身像。他不容许自己在性情上走回头路,每早起来要盯五分钟的毛主席,“什么都要挺过来”,他说。 我说今天谈出点意思来了,吴准笑笑有点意思。最后一圈我们一路无话,末了吴准停住,突然喃喃自语起来:“昔日我曾苍老,而今风华正茂。”我也听不懂,闷声向前。 回了教室我看不进书,毛毛地进进出出。余可可皱眉头,干嘛呢干嘛呢,别跟个夜游神似的。过了个把钟头我看吴准背书包回去了,心里更乱,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好像是周期性的躁病今天犯了,心里直想回宿舍拿手机。一想拿手机我心里更慌,原来放假也没想过要手机,今天却只想快点回去开了机,好像怕错过什么。琢磨半天我意识到自己是想和孟晓微说话,迷迷糊糊地往宿舍走,心里又怕她早早休息,脚步不自觉地快了。拿到手机我想半天不知道该发什么,孟晓微倒突然要我看部电影,我问,你怎么就知道我会用手机呢。她说;“我就是知道。”我说吃你的蛋糕不是故意的,她说你是故意的。我说:“有人都不正眼看我一眼,我自作多情吃了有人的蛋糕。”她又是一番长篇大论说自己如何讨厌何北北,我说我和他是一丘之貉,她说你还差点不要脸,不是一丘,隔了一丘。有的时候觉得孟晓微太刻薄,看她依依不饶的样子又觉得有点可笑可爱,我觉得自己都有点可笑了。聊着聊着我脑子就晕乎乎的了,我又是害怕又是喜欢这种感觉,孟晓微俏皮得让人不敢相信,我说你这么和我说话我会飘飘然的,到学校又是板着一副面孔,我还是别当真的好。她说我是倒打一耙,自己面无生色说她不够热情。宿舍里头就我一个人,我站在阳台上吹风,渐渐觉得有凉意,又是校园里那种独享的静。我心里充盈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快乐,把手机关了细细玩味着,又怕它转瞬即逝。夜在我的身边起舞,风跌跌撞撞地从栏杆跑向树梢,又从树梢滑落,跌落泥土的声音清晰可闻。远方稀疏的灯火在仿佛冻结的天边闪烁,路上的人声都让人亲切,我感到一种种子萌发时饱满种壳的幸福与宁静。孟晓微还在发消息,我却不想回复,潜意识里已经感到这是我心灵所能享受到的极限,继续对话未免会让我从峰值滑落。我和孟晓微说睡觉去了,就把自己封闭在这种宁静之中。 床上我辗转反侧,想着自己已经喜欢上孟晓微了,心里又是惊奇又是恐惧。觉得孙敏敏以后自己已经下了那么大的决心,被孟晓微轻易决了堤,又有点不甘心,总感觉是错误的事。我不知道这种情感是不是和吴准说的那种情怀相背,但我可以肯定,我没有办法摆脱。孟晓微的声音比任何一句先哲的话语都要来得生动,这是我无力超越的现实。也许是因为幼稚,我感觉某种崇高的追求与世俗的情感需要二分,乃至对立,在和孙敏敏的这种感情中,我很难说自己有推己及人之心,志气消磨心气愈低,陶醉和堕落的速度都超乎想象。在那种满足感中你感受不到谋求他人幸福的必要性,不过这也只是情感最初的强大话语权,深入后一部分自我能够得到恢复,但总归有些损耗。 渐渐地就和孟晓微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或有心或无心的谈话我想总是可控的,也不敢往更深处想去,就是现在这样也让人觉得快乐了。孟晓微这么个聪明人有时蠢话也不少,我愈发觉得从前是深深地误解了她,也是她深深地掩藏了自己。家庭的变故对孟晓微伤害是巨大的,她的恐惧从那时开始萌芽。知道了我的情况她愈发体贴,前后巨大的差距让我对自己从前的偏见感到内疚,某种意义上的同病相怜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有的时候都要说出口了,什么东西梗在那里,最后变成沉默。我有时想孟晓微其实一清二楚,甚至享受我的这种窘迫不安,在她仍时时流露的傲慢表情里,我有被欺骗的隐忧。但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能满足她的虚荣,我只是个隐形人,她何必需要一个隐形人的追求呢? (五) 隐忧归隐忧,陷进去是不可避免的事,那种兴奋会冲淡脑子里的一切其他情绪和想法,让你无力质疑它存在的合理性。在这种兴奋里我甚至都舍弃想要看清自己的习惯:如果此时的幸福是真实可感的,我们何必要纠结幸福的来源与其延续的长短呢?晚自习下课我和孟晓微就心照不宣地待在教室,等人走光看谁先背书包,椅子弄出声响是提示,谁也不肯说要和谁一起回宿舍。我对这样的桥段从来只有疏离与抵触,细密如丝的这种小心小思在我看来只是缺乏对生活真切感知的年轻的幻梦,陷入并接受它总是某种程度的狭隘与幼稚,是缺乏痛感的自我。在孟晓微前我不可能做这样的反思,更未想到要做,唯一在脑子里盘旋的想法是路太短,很多话刚起个头就被宿舍的嘈杂声掐断了。孟晓微没反应,我也不敢提多走一会。那天下楼孟晓微上洗手间,我在走廊上等撞上毛奇锁办公室回家,毛奇看我问还没回去,我点点头应着,说是在等吴准,他就下楼去了。孟晓微出来我吓出一身汗,我就怕她也被毛奇看见,反应要慢半拍毛奇就会猜个大概了。路上孟晓微拊掌大笑,说她这点警惕性也没有?听到毛奇的声音她就等在门口看我使眼色了。末了她又补一句,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有那回事怕他做什么,她扭头过来看我说:“你说是吧?”我鼻子差点没被气歪,但孟晓微好玩就好玩在这个地方,将你一军死的看你发窘去她就得意了。倒在床上我想着孟晓微的这话,琢磨有没有别的意思在里头,说暗示说提醒都显得我太自作多情,索性不想下去。被子盖住脑袋还是嗡嗡地想,心里是痒痒的感觉,想孟晓微真是把聪明都占尽了,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一转念又想起,她的这种优势无非是因为我已经陷了进来,换了人不会接她的招,说到底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真是。 吴准不久就知道了我和孟晓微的事,直冲我拱拳,我猜他肯定保留了意见,看我在兴头上也就没说出口。那天四个人一起吃饭,何北北又旧话重提,说:“酒色财气,不就这些个事?不争这个争什么呢?吴准你要说你没有你就是虚伪。”吴准说,不否认这种需求,但是也确实有别的需求。何北北不依不饶,问:“你说什么是第一位的?”吴准冲着何北北把手向前摊,朝我们挤眉弄眼,我们大笑。有弱点才是人呢,做个道德高标不值。吴准说,北岛那诗怎么写的来着,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我隐约想得起后面的几句,在心里默念着: 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 我低头看饭桌底下踽踽前行的蚂蚁,心里想我们不会成为垮掉的一代吧。 我和吴准有时候爱说气话,真实的那点东西藏得很深,可是,谁知道那点东西不会被气话被玩笑日渐消解掉呢,如果真实本身的代价我们都不愿意承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会承担更大的东西呢?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黄昏,这是颠扑不破亘古不变没人能够反驳没人能够否认的话啊,你说理解林觉民也只是人云亦云罢了。我必须承认,纵然牺牲的某种东西强烈吸引着我,但我对牺牲的理解是浅薄的也是不切己的,它只是英雄主义下的一个幻觉,在对历史的凭吊中满足着我的想象,增加着我道德上的某种优越感。好像他们对于生死的蔑视证明了他们蔑视群氓的资格,那种轻蔑又隐隐地折射着他们的大悲悯,在博爱与高傲之间,他们构成历史中最光彩夺目的形象,扪心自问:我有那个勇气吗?孟晓微压根不懂这些话,有的时候让我感到悲哀,多年来寄希望于一份来自异性、同一思想层次的理解,真的只是一种虚妄,寂寞欺骗你有这样一份理解的存在,等待你的却只是落空,即使她是孟晓微。 一切好像都是突然。再次经历和孟晓微对谈的这种苦闷让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着迷?即使在最深处不能相通,我对她却已经近乎狂热?看来最亲密的情感也并非要成为最隐秘的思想的出口,原先以为的那种思想和情感上高度的同一也只是一种幼稚罢了。晕晕乎乎我就牵住了孟晓微,认清那种追求理解的虚妄,好像解开我自己心理上投入进去的最后一道锁链,不去深究了,也深究不清。孟晓微就是孟晓微,没有最深处的那种理解她依旧是孟晓微,眼前的她就是最真最真的,我不想空想地去追求那种自以为是的真实了。我询问式地嗯了一声,她没有说话。我说,你这是让我得寸进尺,孟晓微作势要把我推开,我就顺势松了手。孟晓微说,你走我前面。我笑得差点岔了气,我说走前面你倒是安心了,但万一你孟晓微想对我干点什么怎么办?孟晓微狠狠戳了下我的背,说,不要脸。我说:“不要脸才好呢,不要脸就可以干很多不敢干的事了。”孟晓微说:“你话是这么讲,可脸长在你身上,你不会不要。”我掐起右脸的一大块肉,说,我还要?现在就扔掉。她直笑。孟晓微说:“有人有贼心没贼胆,也怨不了谁。”我说,是了是了,孟晓微还是该勇敢一些。她从后面掐我脖子,说好厚的脸皮。 起风仿佛给了我勇气,路灯连缀起来照亮孟晓微的侧脸,我想起我印象中月色下的海滩。她鼻尖圆得像是被细细打磨过,月光轻轻滑向她的嘴唇,好像调皮地逗弄着些什么,愈来愈不自然的喘息中我们谁也不说破风的节奏。我说,我从没有想过。她声音很小很轻:“你以为我就想过?”孟晓微说,其实我也是突然发现的,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怎么对你一下就不是朋友了。我的肩还是一震一震的,手里全是汗,我问她:“为什么呢,我?”她抿抿嘴:“也没有别的什么吧,我说话的时候你总会看着我,让我有被支持的感觉,就这个?”我接着说,我喜欢你肯定要久些,她问,这也要比?我们不再说话了。雪莱拜伦的句子好像活起来,就在孟晓微的嘴角,她发色模糊难辨,却又清晰异常,好像褐色的绸上洒满银箔,扯着我的太阳穴向外一凸一凸,又烫又疼。 不知道吴准会不会把这说成是一种背叛,最高处思想的同一性与否至今是他衡量情感是否真实可贵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会说,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搂着孟晓微我不知道怎么平复,反倒是她显得更冷静,依依不饶进行历史问题的清算。她问:“真的从来没想过?一点也没有?”我说自己糊涂了,想说的是一直在想。她一定要我说个时间点出来,我就把那天在寝室的事和她说了,絮絮叨叨讲了好多我自己都没想过的话,也丝毫没有违和感。说着我突然想明白,有的你觉得滥情的片段,对话双方脸都不红一下,不是真的脸皮厚,而是那个情境里情感怎么表达都是自然的,你不是当事人,所用的标准仍是日常的那种保守态度罢了。 孟晓微比想象中天真好多,即算是那天晚上之前,我也从来没想过她是这个样子的。她很害怕,最害怕的就是做真实的那个她,她说她妈不允许毛奇不允许她自己也不允许,好像一切都要靠不真实的那个自我来维持,她还需要被无条件地肯定,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像个要成年的人。我说我允许啊,她苦笑说你也不会喜欢的。不真实成为习惯,其实也就是真实,孟晓微没有意识到最大的障碍是她自己。有的话一说出来心就抽着疼,我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去安慰她。她有的时候问我,怎么办?她也怕我们的事本身。就算不被发现不被批评不受指责,敏感时段的这种事也已经对她构成极大的压力,对我亦然。她说每次一分开,她心里就会自责内疚得不行,只想躲开我,但是愈躲心里就愈慌,中了邪地来找我,就是一起时候那种兴奋的感觉能够麻痹一下自己,忘掉恐惧。我在这段感情里也发现自己的无力感,心里的某个感觉像潮水一样,来的时候挡不住,去的时候留不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想起我的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说,连父亲的态度我都没法揣度。吴准说关键时候要用脑子思考,不要用下半身思考,自己都觉得太不应该。 吴准听了我的感觉也不说什么,何北北几个知道眼睛都直了。那天回寝听到何北北和隔壁班在聊天,说真是个冷门,我回寝室把他关在外头。他敲门我说,找你的冷门去!除却和孟晓微在一起本身,我不能否认我满足于一些虚荣,在这个有时那样粗鄙的圈子里,这种虚荣会被急剧地扩大,让你成为圈子的中心。孟晓微表面上的那种高傲刺激着不知道多少人的神经,也成为她魅力的一部分。孟晓微自身的热度和我们之间表面性格的差距仿佛有传奇色彩,让何北北非要知道个究竟,他还不时联系起往事来证明自己的先知先觉。我偶尔回想起尼采的酒神精神,想自己现在居然不在沙漠中跋涉,那种苦行与冥思的生活似乎已经远去了,吴准笑我浑身是粉色泡泡。家庭是哲学家的墓地,这话一点不错,世俗的幸福就是真正的幸福,此刻的真实就是永久的真实,我爱,我喜欢,都是此时,都是此地。“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今夜不关心人类。只有一个声音永远没办法抹去,就是父亲背后那个巨大的影子,即算是孟晓微咬我的耳朵时它也不时传来,那是神谕般的叮咛。我梦见我跪在一座倾坍的圣殿面前痛哭,仿佛一个委屈的孩子讨要允诺中的糖果,面前只有一张青铜色的、威严的、不饶恕的脸,他不说话。梦醒,我从未感觉那样的真实。 两种真实相悖吗?哪种真实,是真实的真实呢? 奶奶走了。这个真实有些虚幻。二叔没有告诉我是癌。医院的路上我不敢哭,好像只要一哭就没有办法挽回,不哭,奶奶也许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她的嘴微张着,像平时她睡熟时那样,护士和医生进进出出,把我挤得一怔一怔。生死于我早已是旧课,从前还更为惨烈,但今天却仿佛是更大的一种悲哀。奶奶还有意识的时候同二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他知道,这就是她,最后一刻还是她。二叔和一众长辈分外冷静,抬着奶奶的下颚,让嘴巴闭紧;抹脸、抹身子,好像是预设的程序一般有条不紊着、环环相扣着。莫奈在妻子死前什么也不做,竟给垂危的妻子画了一张像,生死是应该被格式还是不应该被格式呢? 灵堂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生死疲劳,都在牌桌。跪的疼了我就到奶奶面前看看,没有一点痛苦,她面色如生。好像有一堵我面前的墙静静地塌了,我面前是愈见清晰的死亡,泪水糊不住已经破碎的东西,那些大人们早习以为常。看见那些飘飞的冥币,像极了那些振翅而又折翼的蝴蝶,把真实的东西燃烧到另一个虚无的世界里去,人总喜欢把那些自己所不知道的,煞有其事地当作真实。这些蝴蝶比吊唁者们更加真诚,它们美地燃烧、美地飞舞、美地消逝,虔诚地在一个睡去的生命前完成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不过是形式的完成者,为灵堂平添虚伪的肃穆,互道些关于生活,平庸的感叹。我自知该对这些前来的长辈怀有一份尊敬,却又无法接受他们言语掩饰下那丝毫不在意的轻浮与漠然,在此地展现这种虚伪在我看来并不亚于侮辱。但想想谁会在乎奶奶这样的老人的死活呢,我所经历的情感他们怎能痛切地感知与理解呢?亲戚或余戚,他人亦已歌,只是如此,而已。我想起最后一日下楼,怎么就没回头看她一眼,我明明知道她会站在门口,一下头也不回,泪流下来,那个画面就不断清晰。流进嘴角我就想起她从前每天为我准备的豆腐脑,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热度就是那么刚刚好,白白的瓷碗上勾着蓝纹,甜。香。蒲扇凉席,夏夜的故事,都一下成为触碰不到的远,就不会再有了,我憋住不想,心还是抽着疼。孤零零地就恨起来,无力地、用力地恨起来,冲着那尊青铜像大吼,觉得所有允诺都是一场落空,无端地承受这些苦难也不会有结果,恨得狠了就笑起来,觉得牵挂都了断了,也就无所谓有坚守了,夺走他们也就夺走我身上所谓的不多的美好了,理智在劝我,我挣脱出去大喊:谁对我好过?谁?我一点点在乎的没了,就没有别的在乎的了,好像一无所有才是真正开始拥有些什么。奶奶走了。暗金色在远山盘旋,我好像看见炉子里燃起的火焰,我面前扬起飞尘,我说,都没有了。 ????(六) 把思考的起源解释为走神,我以为未必是对思考的一种贬低,它似乎在说明人不满足于现实的那种追求,时刻产生着持续着。从这个角度思考孩子的开小差,其实反映着他们生命旺盛的内在追求,不接受,不满足。成年人与其说是因其增强的自控能力筑牢了思想的堤坝,不如说是对现实的接受与认同,内在追求的一种衰竭和枯萎捆住了飞翔的心灵,这样说来,不能走神是可悲的。无数人费尽心思依靠物质追求所谓自由,并认为所得到的行为权利、非常享受即自由本身,但他们心灵的疆域何其有限,连面对一丛玫瑰走神的力气都没有。 这话不可能对毛奇说,我自知理亏。他找我谈过几次,我状态依旧如此,他急也急、气也气,到底还是心疼我。他说,奶奶愿意你是这个样子?我叹口气,破罐子破摔似地问,还能有什么别的样子呢。很奇怪,我内心充满着报复的欲望,我知道要通过实在的成绩转化出来,但我仿佛又觉得放任本身是一种享受,没有追求,没有想望,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管,我就是这样了,不走也就不疼了,毕竟走也未必能到。一下子从某种东西里头解放了出来。后来我想明白,我希望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ngyedana.com/qydtx/4740.html
- 上一篇文章: 郭德纲,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 下一篇文章: 肖战ldquo脑残粉rdquo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