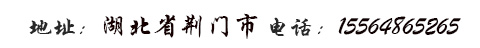青年作家2018年第12期刊发中篇
|
像是有什么感应,门外有人从窗台轰然跌倒在地,似乎瑟瑟发抖,我反应极其敏捷地将黄伟拉到身后,仓猝间,我猛地拉开门,跳进院子,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躲闪不及,额头被狠狠地砸了一下,他感到一阵剧痛,不由地冒了火,一拳狠狠打过来,我躲过身子,他趔趄了一下,黄伟拧开灯,他慌不择路往院子外蹿,被我挡住了,是朱俊。他大口喘气,低下头,是俊芳姐让我跟着你,怕你出事。狗屁,董和兴幕后操纵你,怕黄谋死了,他一分钱要不回来,对不对?我冷笑一声。黄伟用手背擦了擦下颌的冷汗,藐视地瞟了朱骏一眼,喃喃地说,看来我得找这个姐姐谈谈了,中那个老东西的毒太深,苏南,他是什么东西?我妈对他那么好?看来小红楼保不住了。 钱大妈心甘情愿等他十几年呢?黄谋是什么人不重要,关键是你要报复他,我又点燃一根烟,黄伟夺过烟,吸了一口,呛咳几声,半夜里的寒风,发出呼啸的声音,像有人在吹口哨,我踹了朱俊一脚,让他滚蛋。黄伟说,我白问你了,算我没来过,她扔掉烟蒂,站住,黄谋不管怎样,都是你父亲,对他好点,他快死了,我直瞪瞪地盯着她。用不着你来教训我!黄伟眼圈红了。 医院的重症病房,钱俊医院看老爷子,我心里乱,推辞了几回,正好那阵子车间的日本进口的帖蒸汽设备正式运行,需要一批进口的机加工配件,市里的重点企业到处搞技改,本年度的外汇额度超标,市外经委要求厂里攻坚克难,自己想办法。田汉林召开职工动员会,组织技术力量,我又被弄进技术小组,不过组长换成黄伟,钱俊芳请假服侍黄谋。黄伟虽然在日本实习过,只懂图纸的技术翻译,别的一窍不通。可她对别的工人亲切善意,对我却像换了个人似的,语速急促,口气坚硬,声音却越来越幽远。 那天在车间,她还真像个领导,弄得我有点狼狈不堪,看好,轴尖处的倒角R等于0.5,倒的是圆弧角,C是倒角的意思,0.5是圆弧,明白了吗?模具马上车出来,日本的外商还在宾馆里等着检测呢,她自感说得畅快,暗自得意,以为一下子能撂倒我,图纸边全是疙里疙瘩的日文字。我的确惊得有点屁滚尿流。我强作镇定,你的鼻尖长得好看,是倒角还是圆弧呢? 严格的意义上讲,你外祖母是圆弧角,如果你的母亲是倒角,那你就是漏斗! 那你在图纸上签个字吧,马上齐活。我讪讪地笑了。 黄伟捂着胸口干呕了两下,刷刷签上名字,扬长而去。我不再辩解,咬牙切齿地望着她的背影。我怀揣图纸,医院,病房的过道里,我掏出图纸,钱俊芳没有丝毫意外,对着图纸指点了一番后,数落我,哼,你说了那么多废话,无非要解释那晚的龌龊事,还死要面子,我虽然不是工程师,对付她那点雕虫小技,我早领教了。 大姑娘聪明,小生佩服,我赶紧递上去一个巴结。钱大妈招呼钱俊芳进病房,俩人给黄谋喂排骨汤,黄谋喝得香甜,砸吧着嘴,艰难地称赞,富人喝燕窝汤,穷人喝排骨汤,养人。钱大妈白了一眼跟木桩似的我,给女儿使了个眼色,俊芳,B超室的马主任正和几个医生给你爸会诊病情,X光片你去取一下。我自讨无趣,悻悻地转身,钱俊芳忽然掉过脸,妈,我和苏南想和您说您点事儿,请您尊重一点苏南。 哼,什么叫尊重?我嘴刻薄,心里宽厚得很。 妈,请您以后别再为难俊芳了,她也不容易。我忽然冲动地脱口。 别这么称呼,我起鸡皮疙瘩,以后你别纠缠钱俊芳就行!你俩在一个车间,你还准备要耽误她多久?朱俊家把彩礼的钱送来了,她爸看病的钱也送来了,你一个劳改犯,我们母女已经对的起你了,你穷得叮当响,以后再也别为难我们!钱大妈眼光沉下来,眼眶有点红。我慢慢闭上眼睛,强烈的疲倦和寒意袭来。钱俊芳气鼓鼓地反驳,妈,是我在纠缠苏南,这是我个人的事儿,您和爸要是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我准备把我那个破院子和单间房抵押给房管所,看看能不能凑点钱,我一横心,索性补了一句,希望钱大妈发怒,把话都挑明,我的心也干净了。黄谋的喘息轻微却十分清晰,苏南,内不治喘,外不治癣,我多活一天就是遭罪,我不为难你,可你也得答应我上次喝酒给你提的要求,另外记住,你父亲叫苏里,我在广州倒腾服装的时候,他给过我一笔启动资金,所以你不欠我什么。以后遇到麻烦事儿你可以找黄伟,找你爸,仅此而已。可能药物的作用,黄谋一气呵成,胸腔只发出几声沉闷的零散的咳嗽声。 事情完全颠倒。钱大妈阴沉着脸,钱俊芳惊骇地张大嘴,不敢询问下去。我呆呆地沉默了几分钟,脑子混乱了,彻底混乱了,像一块巨石从天而降,把我砸懵了。 是祸躲不过,那天喝酒麻子后脑勺让我开了瓢,医院诊断报告书是轻微脑震荡。他赖在病床上,让朱俊捎话儿,医院谈谈条件。这之前的医药费、住院费、营养费和其它乱七八糟的费用都是黄伟替我一次结清了,所以我搜肠刮肚,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医院前,我打了电话给黄伟,节气阀的磨具已经车好了,医院看麻子。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她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我能想象她似是而非的神情,这让我着迷,上大学时无数次感受过。 医院的单间病房。麻子摆摆手,朱俊带上门,老实地站在门外候着。麻子冰冷的目光盯着我,一字一句迸出:我要撒尿。我连忙拱手,兄弟,你是金蝉子转世,道行深,我降不住你,服了。我从弹簧床下摸出白得刺眼的尿壶,出于心理上的一种阻断意念,掀开被褥,将尿壶探入麻子的下体。麻子龇牙咧嘴,舒服地打了个哈欠,我重新端出有些沉的尿壶,他的目光有些温柔,喝吧,喝了尿,我不起诉你故意伤害。我并不意外,附身问,你真不起诉我就喝。麻子眯缝着眼,在阳光的氤氲里获得稍许的惬意和睡意,他点头,我是认真的。那我也是认真的,你立个字据吧。空气在那一刻凝结。麻子足足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嘿嘿,大学生,你真把我当大傻啊?忽地,我狠狠推开麻子,他从床上倒下又弹起来,床沿发出沙哑的弹簧断裂声,来,用尿壶砸!他掩嘴笑,看,谁来了。朱俊推开门,将黄伟让进屋。我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弹出眼眶。 黄伟并不理我,让我出去,声音短暂清脆。我束手无策,身子依旧呆呆地没动。黄伟沉稳而微笑地坐在床沿一角,从包里掏出小红楼的房屋契约和几页纸,在麻子眼前晃了晃,泰然自若,我和苏南不是夫妻,我俩合作,纯粹是民事赔偿,你要是翻脸,一分钱都拿不到。麻子会意地奸笑,俩人开始嘀咕,黄伟的语速渐渐加快,语言变得像质地良好的丝绸一样柔滑。麻子居然不住点头,最后我惊恐万状地看到麻子居然在那几页纸上签字画押。我恐惧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正浸泡到高粘度的糨糊当中,无力挣扎。尤其麻子最后几乎贴着黄伟的耳朵喊,你看着办吧,一万块钱磕一个头。黄伟没有意外,她的双腿正在并拢,她的腿正在变成一条鱼尾。我闻到了一股茉莉花的香味,这种味道一定是从她身上弥散开来的,她姿态优雅地跪下了,眼睛一如既往凝视着病房的窗外,天色蔚蓝,大雨已经结束,空气清冷,有一种晶莹欲滴的感觉。除了干呕了两下,黄伟下跪的动作是那么温存而细腻。我的心在滴血。 我浑身发抖,冲上前,揪住麻子的头发,被朱俊一把抱住了,黄伟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往门外走,朱俊在背后调侃,苏南,你他妈就是个吃软饭的种!连女人都不如。我不再辩解,舌头像被一根钉子死死钉在墙壁上。我不敢抬头,黄伟正温怒地教训我,你是不是觉得你长大了,别人就认不出你了?小羊羔长大了还是羊,不是狐狸精。 鬼使神差,我俩竟然走到大菜市干涸的半截小桥头边,黄伟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边那口井,我从她身后跟随过来,她内心似乎在挣扎,表情复杂,我涩涩地说,麻子不是个东西,你不该把小红楼的钥匙给他。她呆板地靠在石墩边,木然地说,我怀孕了,既然我帮了你,医院,帮我签个字,把孩子做掉。怀孕宛如刀子一样在剜我的心,切割我的神经,我嘴唇翕动了一下,你承认我是你男朋友?那你国外的男朋友——,她截断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你做完手术,你妈知道了怎么办?钱俊芳和田汉林知道了又怎么办? 田汉林不敢,他有把柄在我手里,我已经告诉他不干技术组长了,你只管找钱俊芳请假。我不理解为什么她不让我找田汉林。 那好,我帮你签字,请假,租房子,我把手插进衣兜里,掏摸了一下打火机和烟,忽然又止住了,身子仿佛被强大的电流击中,抽搐了一下,又一下,我浸泡在这种感觉里,说不上是痛苦、麻木还是幸福。 从医院做完手术回来,我不放心,还是让黄伟回到我的破屋里猫着。我浑浑噩噩想了半天,决定还是去钱俊芳的寝室请假。那天午休,我撩开石墨蓝棉帘,钱俊芳坐在床头,重重地喘着气,脸色苍白,像是经历了长跑,浑身微微打颤。我以为她病了,凑过去,她手里捧着一本书,那是《包法利夫人》,她瞥了我一眼,艰难地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爱玛的很多行为我不理解,可是看到她死,我还是难过了。看到她丈夫卖掉房子,我的心也跟着碎了,多奇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同情的是谁。我无心听她说教,赶紧替黄伟请假。钱俊芳眼里有光,一闪一闪的,叹口气,你俩合伙来骗我。 她告诉我她母亲生病了,她得回去陪护两天。 狗屁!钱俊芳失控地咆哮。 你怎么能骂人呢?我怯弱地望着她。你俩拿我不当回事,我就不能跟你喊两嗓子?钱俊芳盛气凌人,恶狠狠地将书甩在我脸上。 那怎么了?她妈没病啊?她没陪护她妈?就算这样,那也是她骗你,她这么跟我讲的,我这么跟你讲的,你冲我发什么火呢?隔壁周围有不少男女青工破门而入,围拢过来。 钱俊芳憋了一口气,你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和她有一腿!她暴怒不已。 那好,我俩到厂党委会说清楚去,话音刚落,田汉林虎着脸闯进屋,钱俊芳颐指气使地对着周围喊了一嗓子,都散开,干活去! 都别走!田汉林一摆手,钱俊芳愣怔住了。她张张嘴,想辩解,可开不了口。你身为车间主任,技改组长,怎么能这么草率地下结论?在大家面前公开地指责下属,成什么体统?谁跟谁有一腿?这种事是张嘴就来的吗?黄伟要是知道了,她怎么面对车间工人?钱俊芳哆嗦着嘴唇,浑身发抖,她不理解田汉林为什么会拿她开涮?此时此刻,她这个车间主任的颜面丧失殆尽。田汉林目光咄咄逼人,我们有亏黄伟同志啊,这套从日本进口的帖蒸汽设备,是我们厂打翻身仗的生命线,光一期的注册资金就投入了两百万,黄伟为了这个项目,到省里、部里立项,最终确定企业的性质为中外合资,为厂里节省了资金,她多次代表市领导和日方的投资人苏里先生谈判,才有今天的收获,钱俊芳不清楚田汉林哪根筋拧错了,哪根神经搭错了,她深深瞥了我一眼,不管不顾穿过人群,我听到远处钱俊芳凄厉的哭声。工人们知趣地散开了,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眼前一片金光。苏里三个字让我坐立不安,我摇了摇头后,捏紧拳头,撑着桌子站起身,慢慢走到门边,回过身,阳光从门外斜射进来,田汉林的脸上一片幽暗。 时满一周,为了避免感染发炎,黄伟白天一直在我给她找的私人小诊所输液。她依然呕吐,不能进食,医生将一根长长的管子朝她的鼻孔插进去,她挣扎着,仿佛被电击着了似的,大口大口地喘息,泪水从眼眶里憋了出来,她抬起胳膊蹭掉,不想让我看见。我装着没看见,伸出手,摸摸她的额头,她的右面部肌肉像石头一样僵硬,嘴角看起来明显斜歪,一丝清凉的口水从嘴角缓缓流出。我在自己的小破屋里,学会了用胃管给黄伟喂食。大米粥,芹菜汁,果汁,有时候是鸡蛋花,牛奶和面条。喂饱了,黄伟睡得很沉香,有时候醒来,眼睛亮晶晶的,像个孩子;有时候眼神又非常空茫,像个老人。她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醒来时第一个动作就捏着我的胳膊和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反复数着,反复看着。她手腕上的手镯泛着幽光,屋里陷入沉静。我看着她的脸,眼里像星星一样晶莹的泪。她说,我们好吧。 李为民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ngyedana.com/qydcd/2874.html
- 上一篇文章: 大江东一位妈妈摔成轻微脑震荡,看到
- 下一篇文章: 小秦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