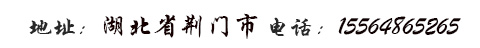西郭风情故事系列红白求恩
|
在加拿大有个做医生的老头,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他没有被日本鬼子的刺刀捅死,而是死在自己的手术刀上(做手术不小心划破自己的手指,感染了细菌导致败血症而死)。延安的毛泽东先生获此噩耗很难过,整夜不睡,抽了一大包烟,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从此中国人知道了有一个外国郎中叫白求恩,这老头是个好事做绝的人,是个高尚的人,是个纯粹的人。 在西郭下浦桥也有一个自称为“白求恩”的老头,也做治病救人的行当。人家那个白求恩有真功夫,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而下浦桥的那个“白求恩”是个江湖郎中,一般的头痛破伤冷、泄肚、流鼻头水、打饱嗝、脚抽筋等等小毛病,他能包治:柴胡、百合、板兰根、大青叶、葛根、前胡、甘草、外加几根葱白,煎服,三天不能洗澡、一个礼拜不许同房,基本上男女老少都能治好。西郭外方圆好几公里内的人,都知道下浦桥有个开草药摊儿的,顺便能看点小病的郎中叫白求恩,除了得上会“单下死”医院外,一般小病都去找这个白求恩。其实这个白求恩就姓白,喜欢喝白酒,洋郎中白求恩是他的偶像,于是索性就称自己为西郭“白求恩”。 白求恩没念过什么书,草药摊儿也不是祖传的,师承何门何祖,不得而知。可这小老头心怀祖国伟大的传统医学,倒是肯下苦功,背熟了许多实用的药方汤头、能说出六味地黄丸主要疗效是补肾、知道最著名的中药材是丹参、至于《黄帝内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经典医书药籍,我想他不是很清楚,但要说起女儿红,老酒汗,生头酒,米醴琼,他心中的小兽即刻窜了出来:几斤米,掺几斤水,加几斤黄衣酒曲,他了如指掌;女儿红喝了口会干,生头酒下肚会上头,老酒汗泡重五的杨梅,那才是人间佳酿,半斤下去会成仙,隔壁寡妇嫩奶比平时好看,说什么也是臀霸。白求恩平时不大爱说话,就是“白眼烧”过肚后,话就从肺里出来,打饱嗝似的成串打上来。有一次在摊儿头公开言论,说毛主席不是红太阳,他老人家也怕烫。为这句酒话,公社和居委会查了他家祖宗三代,幸亏他根红苗正,祖上不是抬棺材的就是解板老司,没有一个是“地富反坏右”,才使得这维持生计的草药摊儿能继续开下来。 白求恩几乎没有朋友,就是一个住打索巷巷臀做圆木家生的和他最要好,也是个五十多岁老头,喜欢喝红酒,自称红求恩。这俩老头几乎每晚都在一起喝酒,白求恩一斤“白眼烧”,红求恩两斤老酒过后,两人就搭肩搂背缠在一起,腾云驾雾,半仙半兽,出现在西郭摊儿头东西两侧的古街小巷之中,成了那时因娱乐不足恋爱不足食物不足性交不足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寂寞夜晚难得的一道风景线。后生们一见红、白求恩,开心的话题,能激发肾腺素的话题马上就来:“阿公,你新妇娒生爻还好吗”?白求恩两眼立马放红光。“新妇好兮好”。“新妇奶水足吗”?“足兮足,小细儿吃爻还多,阿公吃”。“阿公你訾那能吃”?“阿公用嘴啃”。又问红求恩:“阿公,嫩奶臀摸爽啊还是阿翠的臀摸爽啊”?红求恩一边打饱嗝,一边色迷迷地说:“嫩奶臀大,好!摸摸遍,蜡烛也着四支点;阿翠臀糊糯,西门打一下走啦东门还在抖”。说完哈哈大笑,俩老头爽朗的笑声响彻在寂静空旷的小巷上空······。一曲广播里播放的告别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过后,这时,街空人绝,除了昏暗的路灯,因电力不足发出“嗞嗞”的声响外,陋街古巷的石板路上,还有两条头尾交缠的黑影拖在地上,时长时短。俩酒头人在仙游。 白求恩平时不糊涂,他明理,知趣,认清形势,神头灵清。他知道,如今地面上人要想存活,一靠酒,二靠手,三靠毛主席,四靠劳动力。酒、手、力都有了,剩下的就靠毛主席了,所以白求恩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毕恭毕敬,比他祖宗的牌位还敬畏。草药摊儿里有一尊毛主席半身的石膏像,旁边墙上挂一红布,红布上别着大小不同时期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摆放在草药摊儿的正中央,像如今酒店里或者台湾佬香港人开的公司里关云长的神龛,给人一种神秘的前进力量。 一天晚上,红、白求恩两人在草药摊儿里喝酒,高兴啊,激动啊,亢奋啊,红求恩不知何故一挥手,不小心把那尊塑像撂倒地上,砸碎了。晴空一声霹雳,俩酒头人立刻像是被万钧雷电击中了,酒吓醒了大半,老膀胱里一阵阵尿急。白求恩平常上下起伏的喉结不动了,俩人四只醉眼相视,半响不会说话。那年代,谁砸碎了伟大领袖,革命群众就砸烂谁的狗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啊!是大事,按公社张书记的说法,是政治大事,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 訾那妆啊?红求恩吓得旋螺陀似的在地上打转。还是白求恩比较镇定,他呆了半刻,拿起门后的扫帚,把地上的碎片扫起来,一丝一片地扫起来,然后用旧报纸包好。让红、白求恩苦恼的是:这些碎片掼狃宕去呢?不能掼垃圾堆里,否则明天西郭马上会出一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连市里的人都会来的。掼到瓯江还是大桥头九山湖里,能行吗?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不管掼狃宕,革命群众都会组织力量动用一切手段,把反革命给揪出来。这可是该天大的事啊?白求恩左思右想想不出办法,最后来个缓兵之计,先把这包东西藏起来再说。他对红求恩说:“把镬灶间里楼梯搬来”,红求恩搬来一张旧竹梯,白求恩拿着那纸包,吃力地爬上,准备把这包东西藏在墙体和瓦椽结合部的缝隙里。那缝隙空间窄,东西不容易塞进去。白求恩个子小,手短,掂着脚尖,全身发抖摇晃,毕竟年龄大了,又喝了不少酒。当把那包东西硬塞进去时,白求恩一脚踩空从竹梯上摔了下来,右腿骨折了。 草药摊儿关门歇业,白求恩右腿打上石膏,在家休养疗伤。伤筋动骨一百天,闷闷不乐,还不能喝酒,这比死了亲爹还难受。红求恩也不爽,每天提心吊胆,一天三四次狗巡坑似的在白求恩家门外转悠,生怕屋里瓦槽出什么纰漏。白求恩不喝酒,红求恩独自喝没了味道,酒再好再多喝也喝不出那种神韵。这样整天担心忧愁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红求恩找白求恩商量不如去公社主动投案自首,长痛不如短痛,就是判几年也值得,心架每天搭着,何时是个尽头?红、白求恩俩老头想法一致,于是红求恩弄来一辆三轮黄鱼车载着腿脚不灵便的白求恩去公社革委会主动交代问题。 公社张书记请示上级,结论定性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红白求恩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考虑他们主动交代问题,按坦白从宽的原则,俩人先回去等候处理。红求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像老娘客生落个大脚娒。别人问红求恩公社给的什么罪,红求恩说不大懂,好像是“现行番茄”。许多人也不大明白,如今罪名真多,”现行番茄”是什么罪啊? 一个礼拜过后,公社革委会通知红、白求恩到公社,宣布事件的最后处理决定。张书记说求了许多情,说了不少面子,最后决定每天上午六点到十点,两人挂牌,站在摊儿头十字路中间,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斗,从明天即刻开始。 西郭摊儿头是一处具有广场功能的十字街口,除了西郊小学操场算这里最为丈宽空旷。周边有“宝弟水果摊”,“阿十点心店”,“阿青裁缝店”,“国营烟糖商店”等等;白日里这里闹热非凡,说书的“暯瞠福”,讲笑话的“银洪”,放西洋镜的“老彭”,乡下人的糖儿担,捏糖人儿“聋彭”,买“雪花膏”的银翠,做棉花糖“水推瓢”等品牌小贩都聚集这里讨生活。周边挨家挨户的屎盆壅桶头天夜里睡前也都集中这里,等第二天凌晨环卫处里的“端壅客”来集中倒掉,运走。天刚亮,太阳刚醒来,从东面懒撒地把清谈的光投在这里时,集聚摊儿头所有的屎盆壅桶的盖子都已被“端壅客”开掉。他们天没亮就起来工作,腰围绿皮短围裙,左右腋下,各夹屎盆一个,疾步如飞,麻利地走向路口的那辆大粪车。“端壅客”们倒粪水的劳动姿势优美,流畅,一气呵成,劳动创造了世界美好。 红、白求恩接到去摊儿头接受批斗任务时,态度非常诚恳,工作勤快认真。每天天蒙蒙亮。红求恩就用三轮黄鱼车驮着白求恩出来。三轮车停在屎盆壅桶中间,白求恩腿脚还没好利索,坐在车上,红求恩站在车前,脖子上端端正正各挂一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牌子很大,也重,每天挂三个小时是力气活,可俩老头觉得这样最好不过了。 批斗刚开始一段时间,每天还有几个带红袖箍的人过来查看,后来没来人了。如何打发这段时间,成了红、白求恩开始思考的又一个问题了。不知是谁的提议,他们一致认同,喝酒才是让时间飞转的最有效的办法。于是他们第二天出来时,顺便偷带点私酒,批斗时,以牌子做遮掩,利用低头机会,偷吃“天光酒”。开始一点点,后来一整瓶。水果店宝弟经常塞几把“槐豆子”“落花生”放俩老头衣兜里;水产店阿池老司也经常弄几条溪鱼干塞俩老头手掌心。革命群众心一软,红、白求恩胆就放任了。他们在九点半以前基本喝得是“五洲激荡风雷急,四海翻腾云水怒”了,他们不觉得自己腿站肿了,腿站麻了,只觉得做人有意思。 有天早上,下雨,下大雨,初春的风,孤冷,冷意沁入人骨。我撑着油布雨伞去大桥头小学读书,在摊儿头见到红白求恩。摊儿头稀有行人,红白求恩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挂着牌,一站着,一坐着;他们手不利索,身子在颤抖,他们还象平常一样,头一仰一低,他们在喝酒。他们喝进的是冷酒,呵出去的是热气。热气一口,一口口,不散,像云雾般的绕在他们头顶上·······。 这个场景刻至今我还记得,时常还会在我脑子中电影般地重放,也时常让我涕泪沾襟。 (西郭风情系列故事,属于虚构,如有雷同,切莫对号入座,均当唐讲视之,不必当真。)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ngyedana.com/qydxw/1320.html
- 上一篇文章: LXPLCDSS第25期
- 下一篇文章: 柳翠芹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