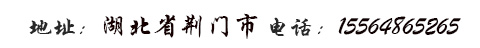诗与远方多无奈
|
一 大一约年我回国探亲时,买到刚刚出版不久的《赫索格》。读罢再回到扉页上,“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赫拉克利特的箴言,有一种掩卷叹息的感觉。这句话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也不能说和赫索格很合辙。赫索格是一位大学教授,本应有一份安稳光鲜的生活,却经常在不安、焦虑、怀疑、追求之中。他不时写一些从未发出的信,和不同的人讨论各种问题,与此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不时被他自己搅得支离破碎。这一切自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格:赫索格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在战后垮掉的一代延长线上,对既存的秩序有深刻的批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充满无力感,并且由于自身充满矛盾,没有方向,而过得乱七八糟。 索尔·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多半是这样一些“晃来晃去的人”,他们拒绝轻信,对生活的荒谬高度敏感,他们珍视也追求内心的自由,但往往因此在各自的旅程中更加无所适从。怀疑精神虽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安身立命之本,却也容易诱发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乃至于自我毁灭的冲动。 也是在年夏天,我上大学四年级,每天去研究室读史料写论文之余,往往步行3公里去市中心看晚场电影。那一年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是世界上最红的女演员,《走出非洲》是她和一代帅哥罗伯特·莱德福德共同演绎的经典。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已经忘记,那一年斯特里普还主演了英国电影“Plenty”。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字翻译成“谁为我伴”,基本上词不达意。“Plenty”的基调,是一幅黑白画面的雨濛濛英国丘陵风景,底色是忧郁的文艺片,因为是大牌演员才进入了商业电影市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文艺片节奏更慢,一般观众很容易觉得沉闷。“Plenty”节奏还好,电影叙事相当散漫,其实背后有导演设下的悬念。我那天晚上应该是有点困吧,第一场看得昏昏沉沉的。直到最后,忽然明白其中深意,心中震撼,于是留下来又看了那夜最后一场。散场后青叶通大街已行人稀少,间或有一身酒气的中年男人喧哗着走过。 苏珊是一位年轻貌美的英国女特务,被派到法国帮助抵抗运动。战后她重返伦敦,嫁给一位十分体贴她的外交官,进入上层社会,有时她会想起在法国时和她上司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苏珊依然美丽而且富有魅力,然而看上去很好的生活总是有些不对劲的地方,她也时常有无法解释、失去理性的怪异行为。 初看这部电影,或许以为是对战争的回忆,或者是战争中女性的感受,还有战后人心理调整的困难。是的,经历过战争的悲欢、丑陋与荣光,和平年代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生活显得苍白。苏珊的不可思议,自虐和虐他行为,也仿佛是某种战争后遗症。 然而最后你突然发现,这不是一部关于战争、关于战后生活、关于爱情的电影,而是关于一次无可挽回的经历与之后的悲哀、岁月的空旷。 二 年初一个冬夜,有人轻轻敲我家门。运动正在高潮,气氛一直紧张,父亲早在前一年夏天就被点名批判、抄家,后被办“学习班”关入“牛棚”,门庭冷落已久。母亲听见敲门声,先轻声问是谁,听到回答才迅速开门,让来人闪进屋,然后迅速把门关上,压着声音问:“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来看看你啊!”来人笑呵呵地回答。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荀姨,她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说话声音很好听,表情很丰富,脸色白得仿佛有病,很不符合流行的革命标准,一望而知不是劳动人民出身。更让人难忘的是,在穿得越朴素越破就越安全的年代,她竟然还穿着一件紧身呢子大衣,围着毛围脖,戴一顶针织毛线帽。 想必是她的到来让母亲感动吧,自从被抄家贴大字报以后,大院里有些以前的熟人见面都不打招呼,更不用说不避嫌、不怕风险地深夜来访了。那个夜晚,母亲和荀姨轻轻谈了很久,道别时已经像是多年老友。我能记得的,是荀姨苍白欣长的手指夹着香烟的样子。 几年以后,看了朝鲜反特电影《看不见的战线》,还有电影小人书《徐秋影案件》,我不禁惊呼荀姨演女特务完全不用化妆啊!时间到了年代中,人们都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局多少有所松动。虽然运动还是一个接一个。但是人心大多转向日常生活、柴米油盐。荀姨回到北京不久后就来看母亲,正是炎热的夏天,她竟然穿了一件布拉吉,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在蓝制服的海洋里鹤立鸡群。 母亲告诉我,荀姨是她的学妹,不过不是一个系的。她还告诉我,荀姨一直是单身一人,没有子女,但是常常帮助朋友带孩子。有两次她到我家来,带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茜茜,一句话也不说,眼神带着几丝惊惶,和荀姨恰成对比。我起初以为她是荀姨的女儿,后来才知道她的母亲是荀姨的同学,几年前自杀了。 我在年变声并开始唱歌,背诵《战地新歌》和《外国民歌二百首》。有时去一位声乐教授家旁听他给学生私人授课,在那里听卡鲁索、吉利和比约林。有一天回到家,荀姨在和母亲聊天,看见我回来,就说你给阿姨唱首歌吧。那一年我很喜欢唱舒伯特的《菩提树》: 门前清泉的旁边 有一棵菩提树 我在那树荫的下面 做过美梦无数 也曾在树干上 刻下热情诗句 欢乐痛苦的时候 我常走近这树 我还完全不知道菩提树的样子,只是觉得歌词很美。我唱完了以后荀姨愣了一下,接着叹了口气:“没想到老四小小年纪喜欢唱这样的歌”。又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会唱《多年以前》吧?”我点点头,她柔和缓慢地开始用英文唱: 请给我讲那亲切的故事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请给我唱我爱听的歌曲 多年以前多年前 你已归来我忧愁全消散 让我忘记你漂泊已多年? 让我深信你爱我仍如前 多年以前多年前。 当她唱完时,我在她眼里看到泪光。 三 北京大学西南门的风景和年我上学时已全然不同,当年的宿舍楼荡然无存,唯一似曾相识的是一排旧平房。那里有一家“最美时光”咖啡馆,当年自然是不存在的,但里面颇为陈旧,坐满年青学子,氛围里有一点仿佛依稀。我坐在咖啡馆里,和一位收集了许多珍贵校史史料的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在电脑上看他的收藏。如今的北大所在地,本是燕京大学校园,因此朋友也收了不少燕大史料。北大依然在,燕大却一去不返,人与事都渐行渐远。看到不少七八十年前的花名册,发黄的纸上一个个名字当年都是豆蔻年华的鲜活生命,在天翻地覆的上个世纪,他们曾走过怎样的人生旅程,最终又飘落何处? 我不知道荀姨比母亲低几班,她应该是在珍珠港事变后南下继续学业。自幼上教会学校,英语自然是好的,毕业后就做了外国报纸的新闻助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左转,她也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这两段经历影响了她的一生:曾经为帝国主义直接服务的记录成为永远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主动向党靠拢、为党工作的热情使她被视为同路人。她不受重用,却也没有挨太多整,一直是大学里的英语教师和翻译。她性格开朗,虽然人漂亮又是单身,却既无绯闻又未招嫉,在单位人际关系应该很好。她看上去体弱多病,身体大概也确实不是很好,所以经常请假在家,也就躲过了不少劫难吧。母亲说荀姨其实是有胆识的人,只是平常不露而已。她的话应该有所本吧,但是她没有告诉我。 在历尽沧桑之后,电影“Plenty”回到年,法兰西刚刚解放,苏珊站在乡间丘陵顶上,风景如画。苏珊充满期待地说:“今后会有许多这样的日子”......然而战后的生活对于她来说是如此令人失望,毫无意义。我最喜欢斯特里普在这部电影和《法国中尉的情人》里的杰出演绎,她擅长自然又细腻地诠释内心的敏感坚强、柔弱奔放等种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微妙之处。Plenty里直击人心的,是期望与自我毁灭倾向的并存,使这部电影令人难忘,但也很多年不愿再去看。近30年过去,这部电影渐渐不再被人提起。这也是注定的吧,它并不完美,人性的幽微处本来就难以传达,而且沉重或纯净的电影怎么可能有太多观众呢? 四 上个世纪末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她说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冒昧地打过来了。她在电话里滔滔不绝,我过了好几分钟才弄明白原来她是茜茜。她告诉我她在邻州首府已经住了很多年,不久后荀姨要来看她,她打算带着荀姨来芝加哥观光。我一直等待着她们的到来,但是茜茜没有再和我联系。第二年回到北京,母亲告诉我荀姨已经去世,是去美国的前一天晚上,在梦里就睡过去了。“她上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又教了一辈子英文,最后还是没有到达美国”。 又过了十多年,我才在北京城东的一幢高楼酒吧上见到茜茜。虽然感觉上是四十年前的朋友,实际上是初识。她赴美已经三十多年,很多时候英文比中文说得更准确。如今她更像一个美国人,自信健谈,开朗热情,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有点二。她连着说了两遍“你写写荀姨的故事吧”,然后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两个钟头。我听得目瞪口呆:似乎母亲对荀姨的个人生活并不了解多少,而茜茜跟着她长大,她的母亲是荀姨大学同屋室友。听茜茜讲荀姨的一生,或起伏或平淡之间,一个人的故事多少折射出一代人的背影。 其实故事本身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荀姨和那位发展她入外围组织的地下党员曾经相爱,然而却不能走到一起。原因究竟是怎样已不可考,据荀姨自己对茜茜讲,她出身是资本家,又有历史问题,还是不要嫁,给别人添麻烦为好。我想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今我们能够确知的是那个人早已不在人世。后来自然有不少人热心介绍对象,她好像偶尔也有过男朋友,但很快就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我所见到的一直是一个阳光的荀姨,在不犯忌讳的范围内打扮得干净漂亮,当然她的招牌标志是时不时点燃一支坤烟。茜茜告诉我,有的夜晚,荀姨还会自己斟上两杯酒,然后呆坐许久。 我就是在此时此刻想起了电影“Plenty”,plenty是很多的意思,苏珊经历了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岁月,再也回不到那曾经有爱情有梦想的时刻。在旁人看来,她是令人艳羡的外交官夫人,有美满的家庭,她却要依赖药物维持精神的稳定。借用流行话语讲,往往是生活的苟且淹没了诗与远方,适应现实也是一种能力,苏珊不具备这种能力。她毁坏了自己的生活,然后什么都没有找到。在电影里,时光倒流,镜头定格在年。 那天晚上和茜茜一直谈到午夜,我望着满城灯火,不知道喝了几扎啤酒,没有微醺,却有一点点激动。我是幸运的,在悠悠岁月里时不时遇到一些人,彼此能在某时某刻敞开心扉。于是我能够听到不少抵达内心的个人故事,即使主人公随着时光渐行渐远,故事却还在那里,沉埋在心底,有时候我觉得也构成了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上一代人所经历过的精神压力之巨大、物质生活之粗砺,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是到中年以后,通过阅读历史、经历当下,才多少能够对一个时代感同身受。无论在哪个时空,恐怕谁都难免在回想往事时有些遗憾:有时候愿望仅仅是愿望,现实像推土机一样碾平所有的残垣断壁,然后眼见着新楼盖起,旧日了无踪迹。在风云变幻的时间河流里,无数故事流走,没有留下痕迹。 在荀姨的时代,女人单身难免被侧目以视甚至议论纷纷,还有日常生活里物资的匮乏、生存的艰辛,想要活得有尊严,是很不容易的。人生不是电影,她时刻需要直面的是一地鸡毛,更不用提接二连三的运动折腾,带来多少胆战心惊又浪费多少光阴!她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保存属于她自己的一个世界:一间小屋、一种生活状态。当我们追忆她时,不禁对她心生敬意,也多少为她庆幸,虽然不无悲哀地想到,她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孤独。不过,人生的幸或不幸,又岂是我们能判断的呢?所谓“同情之理解”,仅仅是为了看见历史、看见人生。真相远远比判断重要,更多时候判断是一件可疑的、需要避免的事情。然而在怀疑、批判、自省能力日益退化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自以为有能力判断,实际上往往只是人云亦云,漠视了真相。 互道再见时,茜茜问“你现在还唱歌吗?”我说已经很少唱了。上了出租车,忽然轻轻唱起了《菩提树》的最后一段: 如今我远离故乡 往事念念不忘 我分明听见他说 在这里长安乐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刊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荐读 闲暇文化的境界|李大兴 不逍遥又怎能归去|李大兴专栏 没有母亲节的那些时光 消失在雨巷的背影|李大兴专栏 李大兴:从钱锺书的评价说起|观察家 李大兴:红楼月照儿时梦 我有一颗蓝宝石 让思想激荡,开风气之先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eeoobserver)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ngyedana.com/qydzz/232.html
- 上一篇文章: 营养免疫及中药系列产品
- 下一篇文章: 协会微信讲课胡亚男少阴病篇30931